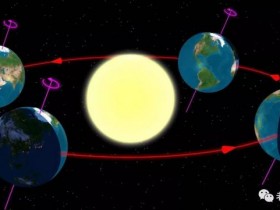引子
清末的陕北,在经历了“同治回乱”之后,越发显得萧条,吏治更加腐败,民不聊生。原本就极端脆弱的官民生态,更加雪上加霜。
从光绪元年开始,这一块荒漠化的土地上,自然灾害层出不穷。这年冬天,黄河自跳桥以下至碛塄地方,冰冻40余里,府谷与保德两岸居民踏冰往来,络绎不绝,这是百余年来罕见的情景。光绪二年冬,黄河冰冻方才缓解。而光绪元年至二年冬春,冻饿而死的饥民数不胜数。
大寒之后是大旱,经历了光绪二年的一般年景之后,到了光绪三年春,一场罕见持续干旱延至秋末冬初,随后,大风伴着大雪在榆林城周边府县肆虐,灾情奇重,饥民遍野。
神木、府谷等县城粮价翻番上涨,而官府征收的粮款却毫无减免的迹象,一时间,大量饥民沿古长城一线往蒙古、山西、甘肃等地逃命,一路上死伤无算。
到了第二年,瘟疫又大规模流行起来,史料记载:“人相食,死亡载道”。
灾害频繁,神木府谷一带的民人,已经形成了“走西口”逃荒的传统,往往以家族、整村为单位的大规模迁徙,蔚为壮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大疫虎烈拉传播,府谷全县死亡人数盈千,城关尤甚,道路行人断绝40余日。
流民持续逃亡口外,地方官员无法控制。清政府对于流民的垦荒政策,除东北外,蒙古地方也是“禁垦”之地,然而,对于风雨飘摇的清政府而言,既然无法阻挡流民外逃的趋势,也就只能变堵为疏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绥远垦务大臣在古城、哈拉寨、沙梁三镇设垦务局,开放县北与伊盟准旗交界的“黑界地”,县民领照认垦,分礼、智、信三段,岁租由县代征,每年收银约1600余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将理藩院改为理藩部,派遣民政部外城巡警厅厅长朱启钤为督办内蒙东部三盟垦务专员,在蒙古地区实行“筹蒙殖民,改革图强”为内容的新政。
但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大局日危,上下交困”风雨漂摇之中。在新政实施中的蒙古地区放垦事务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鼓励、放松限制变为全面放垦甚至武力强垦。把移民实边和新政的目的完全放在了搜刮民财,以缓解清廷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上。所谓的新政变成了不计垦务效果的滥垦滥放。
在朝廷政策的鼓励之下,神木、府谷各地因灾致贫的民人们,开始扶老携幼,从黄土高原的各个角落,聚集在长城一线,沿长城和黄河一路向西,去往一个谁也不知道前途命运的所在——口外。然而,到达口外的流民对于朝廷新的盘剥显然极为反感,在突破武力强制的垦荒之后,流民们很快发现:广袤的西北草原和荒漠地带,完全可以避开官府的盘剥,他们四散逃离,在荒芜人员的黄土高原和荒漠草原腹地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隐蔽而又分散的聚居的村庄。
第一章
郝玉元牵着马刚刚犁了南边慢坡的一块地,往回走的时候,村巷里显得格外冷清,流行的疫病让各家各户不断有人被送到北塬壕里。先是郝正林的婆姨四婶子先一天拉了一天肚子,紧接着第二天就吃甚吐甚,连一口水都入不了口了。饶是集镇上林先生的药能起死回生,也无法挽救一脸绿气的四婶子的病症了。
郝正林和儿子拴狗在门口拦住要出门的林先生:“人还是这样子,你咋能走?”林先生皱着眉头道:“我现时也没有啥好办法!”郝正林打着哭腔问:“那咋办?”林先生沉默半晌,终于开口对郝正林道:“这叫虎烈拉,上吐下泻,也叫两头放花,老天收人哩。我是无能为力了。叫拴狗到娘娘庙供奉一副好皮子,顺便在北边壕里把坟扎好。”郝正林和拴狗双双瘫在地上,林先生咬了咬牙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那天夜里,四婶突然就看不见了,总叫人点灯,随后大吵大闹,跟一些过世的人说话,后半夜就安宁了,鸡叫三遍的时候,拴狗就发觉母亲没有了鼻息。
第二个死的人已经不可考,因为染病的有好几个人,究竟谁是第二个死的,已经没有人有这样的心劲计较得那么清楚了。瘟疫开始在整个南塬上传播,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备棺木、请乐人,大操大办,后来就草草了事,到如今死人的这境况,别说安置寿材,主家连卷尸体的席子都觉得多余和奢侈。
持续的干旱让地里的粮食颗粒无收,饥荒下的民人原本就在死亡线上挣扎,而疫病的到来,让原本还有希望度过饥荒的人们,彻底失去了希望。
人们不再讨论庄上谁家死人了,而在惊奇于谁家没死过人,直到死人成为常态,所有人都变得麻木,死人似乎变得跟死了一只鸡、一只狗一样平常。郝玉元为了让老父亲避免被传染的厄运,早在村里第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就把老父亲送到了姐夫家,那是一个孤零零的山峁,几乎与世隔绝,他乐观地认为,疫病不大可能会传染到那样一个山峁上。
曲折的羊肠小道连接着一户一户的住家,郝玉元牵着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遇到。他家是村里唯一一户还没有死过人的住户,当然,郝玉元一直以来也是庄子里最富有的人家——上百头的羊,几十垧地,村里唯一的青砖大瓦房。而同治反正之后,这样的好日子不复存在。先是老父亲外出贩羊皮,被乱匪打伤,随后朝廷不断加收各类粮饷,弄得民不聊生,在榆林城和府谷县城的店铺因为道路不通,早已经鞭长莫及……加上灾祸不断,原本殷实富有的家业,如今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入秋后不久,一场大雪让整个南梁白茫茫一片,郝玉元挺着大肚子的妻子郝氏正在门口纺羊毛线,老太爷的屋子里传来一阵阵的咳嗽声,这是被乱匪打伤的后遗症。
“这两天雪大,不能挡羊,后院仓里有荞麦皮,你先给喂着。等天晴了我再打一回干草,今冬的草料就有了。我到川里去一回,今冬咱大的药该抓了。”
郝氏道:“这么大的雪你不要命了?雪大路滑,万一出啥事了,这可咋办呀!”郝玉元道:“林先生每年九月二十一坐诊一回,其余时间根本见不着人,咱大的病可就靠林先生压治哩!就是下刀子也得去呀。”
郝氏叹了口气:“你把干粮和银洋带够。这一走得几天?”郝玉元一边把褡裢挂在肩膀上,一边穿上羊皮坎肩,道:“得四五天。”
郝玉元在褡裢里面装满了银钱,那是去年卖羊皮换来的最后一笔收入,他把装银钱的口袋扎得紧紧的,一条粗大的羊毛棉裤,裤脚被扎进羊皮鞋子里面。郝玉元冒着大雪牵着白马,就出了自家的院落,奔着一条羊肠小道,在一片白茫茫的群山中若隐若现,渐渐消失了。
大雪明显阻断了人们的行程,瘟疫带来的恐慌也让原本人流熙攘的市集人少车马稀。府谷县城哀鸿遍野,一路上缺衣少食而死亡的流民比比皆是。清家虽然指派了“资恤局”收殓尸体,而这秋日大雪显然让资恤局的官人门早早回家了。
夜色渐浓,雪却下得更紧了。大街上已经落了厚厚一层雪,人马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周边道路上被雪掩埋的流民的尸体只剩下一个个大体的轮廓,一群野狗红着眼睛在拖动和啃食尸体,郝玉元骑着马从旁边经过,野狗也并不惧怕,只是抬眼看看马匹,就继续啃食。
郝玉元来到郝家油坊,店里的伙计看见之后,立即通知掌柜的,随后牵了马去后院。掌柜的把郝玉元让进来:“东家这么晚来,有甚紧火事?”郝玉元拍打着身上的落雪,道:“寻林先生,老掌柜每年冬天的药该置办了。这就是头等大事!”掌柜的点点头,吩咐厨下把火重新点上,热了一壶酒,烧了几样菜,陪着郝玉元坐喝。
大旱的那年月,郝玉元家里只能吃起糊糊的时候,油坊的生意就每况愈下了,不仅拿不回来银子,甚至还要老掌柜的贴补一部分。无奈之下,老掌柜的拖着病残的身子下了一趟府谷,与郝家油坊的账房、如今油坊的新掌柜魏先生签署了协议,将油坊六成的股份转让给魏先生,郝家只吃股息,不再参与油坊的经营。
尽管油坊易手,却并没有影响两家人的交情,每回下府谷,郝家人还是习惯吃住在油坊,而魏先生也每次都应心接待,没有任何怠慢。
酒过三巡,两人都有些微醺,说起当前虎烈拉的事情。郝玉元道:“庄上人快死绝了!连林先生都没有办法,这境况咋收拾?”魏先生没有言语,却招呼伙计从后堂拿出来一块黑褐色的东西,郝玉元见了一惊:“这是……土?”魏先生点点头,悄声道:“这东西化到滚水里头能治虎烈拉,其他仙丹妙药都不管事。而且,对老掌柜的老病有好处!我费尽心机,走了一趟关中才拿到的!”
郝玉元道:“现时人连水都喝不进去,这烟土……能行!”魏先生又悄声说:“化不成水,那就揉到烟锅里头,一天抽上两三口,就把病根去了!”郝玉元点点头,他明白,在这个任何东西都无法起到作用的时候,这种被称为祸国殃民的鸦片,成为庄上乡亲们唯一的生路了。他想了想,现时情况危急,此次下塬,不知道庄子里又有几个人在南坡拱起了坟。他甚至都不敢耽搁,打算翌日一早就去找林先生,开了药立即骑马上塬。
魏先生给他的灵丹妙药,这药效任谁都知道,无论是咳嗽还是上吐下泻,只要用了这东西,立即就能止住。可是贫病交加的庄户人,连一天两顿饭的温饱尚不能自持,遑论这昂贵的烟土了。
第二日一早,雪稍稍停了,天气却更加阴冷,左右沿街的店铺偶尔腾起浓重的白汽。郝玉元就别了魏先生,进了林家铺子。铺子里面已经有了几个等着看病的人,林先生正在给人号脉,见郝玉元进来,点头算是支应了。
号完了脉,林先生拿出备好的药交给郝玉元,就转身回到座位上,给刚才号脉的人开方子,郝玉元还有话说,却苦于没有机会开口。林先生见郝玉元拿了药不走,有些疑惑,就转头问:“还有啥事没交割清楚?”郝玉元掏出一把银洋交给林先生,林先生也只从中拿走两个,道:“再没啥事?”郝玉元欲言又止。
林先生开完方子,对等候的人拱拱手:“久等!”就带着郝玉元去了后宅。郝玉元拿出烟土,问:“这东西能治两头放花?”林先生瞪大了眼睛:“你从哪儿弄来的?”郝玉元不答,只是问:“你只说能治不能治?”林先生盯着烟土点点头:“能!”郝玉元这才放下了心,紧接着又问:“我家老爹的病,能治不?”林先生郑重其事地看了看郝玉元,把他手里的药重新拿回来,又重新开了方子,抓了药,这才道:“有这个方子,就不怕犯忌了。”
郝玉元把烟土掰了一块交给了林先生,他知道,林先生所在的镇上,如今也是虎烈拉最疯狂的时候,而烟土这种东西绝对是紧缺货。林先生千恩万谢,把原先的两个银洋奉上,又抓了两把银洋推给郝玉元,郝玉元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转身就走了,只留下林先生抓着银元不知所措。
郝玉元收好了烟土,还有一小包其他玩意儿,这才从林家铺子出来,翻身上马,空着肚子就回了南塬了。
他一路狂奔,心里如同火烧一般。他不愿意再看到任何人因为这瘟疫而丧命。庄子上熟悉的面孔不断减少,他的心里跟刀割一样。虽然他并不是庄户的官人,更不是甲长里长,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责任把乡亲们从命运垂危的境地拉回来。
他夹紧马肚子,一路狂奔,不知什么时候,雪又开始一阵紧似一阵,他冒着风雪,赶在天黑前,回到了庄上。
在给老爹把药熬了之后,这一天晚上,老爹的病情大为好转,深夜中那让人心里一颤一颤的咳嗽声少了很多。他一阵狂喜。第二天一早,他找到了郝生印:“生印你来,我有个事。”郝生印是族长,算是庄上的官人,尽管年岁比郝玉元大十几岁,却是下一辈的后人,对于郝玉元还是比较尊重的,一方面郝玉元辈分高,另一方面郝玉元为人耿直豪爽,深明大义。
“七叔有啥事你尽管说,我保险给你把事情搁住!”郝生印颇为豪气地说。郝玉元看到他脸上的绿光,就知道这中年族长命不久矣:“我看你气色不对,怕是两头放花了!我下了一趟府古城,从林先生那里取了些药,你敢不敢要?”郝生印一听这话,当时就跪下了,磕头如捣蒜:“七叔你要是把我命救了,我给你烧香磕头立生祠都能行!咱郝家人现时还能不能保住我不知道,但我是族长,我不能殁了啊!”郝生印涕泪俱下。
郝玉元点点头,从屋里端出一个瓷碗,郝生印见里面有小半碗泛着棕黄色的汤药,也不管是否有用,一饮而尽。随后,他往南梁边上走了一截,因为习惯性的呕吐总是在喝下汤药之后不到一刻钟,就会重新从肚子里泛起,再从喉咙穿过口腔直接喷出,郝生印怕弄脏了郝玉元的院子,就转身走了一阵。然而等了一阵,郝生印惊喜地发现,这次喝的药并没有之前那种要呕吐的迹象,反而肚子里面呼噜呼噜响成一片,紧接着是一串响屁放出,臭气熏天,却并没有蹦出绿色的稀屎。这就是个喜人的变化。
郝生印欣喜若狂,跑到郝玉元窑洞里,高兴地说了自己的变化,郝玉元道:“后晌你再来一回,明早再看。”
郝生印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后晌又到了郝玉元的宅子跟前。这在一群窑洞中是仅次于郝氏祠堂的建筑,在所有人还都居住在窑洞中的时候,郝玉元的老父亲已经依靠自己的勤谨和节俭,把一幢青砖红瓦的四合院式建筑盖起来了。
当地人并没有兴建四合院的习惯,郝玉元的老太爷担任郝氏族长的时候,与族人们去过京城。那是雍正年间,郝氏有人在京城为官,官阶还不小,似乎是礼部尚书这类的大官。乡人们刚刚修建了郝氏宗祠,而家族名字辈分却没有延续下来,于是商量着去京城跟这个有学问的郝家的尚书讨一个字辈排序。在京城里,郝玉元的老太爷见到了这种四合院的建筑,觉得比起老家的窑洞,不知道要气派多少!
回到了府谷之后,老太爷把修建四合院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训诫,一代一代传下来,到了郝玉元的爷爷辈,家境渐渐殷实起来,就着手修建四合院。郝玉元的爷爷穷极一生,将修房子用的木料和砖瓦才备齐;到了郝玉元父亲手里,这幢独一无二的四合院才全部修建完工。
一时间,整个府谷城都轰动了,县城的人也不远百余里来到这里看稀罕,甚至一度影响了府谷县城的民居风格。
郝生印又饮了一大碗汤药,又跟郝玉元等人说了一阵闲话,天擦黑的时候,他脸上的气色就明显好转了,体力也好了很多,随手拿着的拐棍也被扔到了沟里,郝玉元见郝生印稳稳地站在大门口的一块石头上,心里的石头算是放下了:这药没有问题,能治病!他随即对已经活蹦乱跳的郝生印道:“敲锣!放快!”
郝生印起身去了祠堂,一会儿工夫,远近的山峁上就响起了清脆的锣声。火把点起来了,在这雪夜里显得格外显眼,火把朝着整个庄子的中心地带——郝氏祠堂。
村里十六岁以上的男丁,每户一人,全部集中了郝氏祠堂里,平日里族里有大事,只有十六岁以上的男丁才能进祠堂。此次,连不大出门的郝玉元的老父亲,也被搀扶着进了祠堂。郝生印一句“发蜡!”就有人抬着蜡进来,等众人把蜡点亮,祠堂里一片灯火通明,在门外的雪地里投下一片火红的颜色。
郝生印点了下人数,这次才彻底明了:因为灾荒和瘟疫,全村九百多号人,如今只余下三百多,死了三百余人,还有三百余人去内蒙逃难去了。郝生印叹了一口气,对郝玉元道:“就这些人口了。你看……”郝玉元道:“你说,你是官人,说话准事,我没分量。”
郝生印点点头道:“夜黑间,我玉元叔去府谷寻了林先生,取来了药草,能治虎烈拉,我是治好了,这阵已经没有啥事了,现时把药发给你们,回去用热水冲泡喝汤,一天喝上三回,就没事了。但是切忌葱、蒜、浆水!”郝生印对一个近门侄儿道:“发药!”
这一块烟膏子被切成黄豆粒大小,分了下去。郝生印道:“明天这时间,都来祠堂里,看看效果!”众人乌拉一下散了,尽管很虚弱,但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看不到曾经的死灰之气,反而洋溢着生存下去的光亮。
鸦片的功效自不用赘述,很多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乡民们重新焕发了生机,第二天夜里,木香、黄连、白术等药草同样以家庭为单位被分了下去,郝玉元这次亲自表态:“这药同昨夜间发的药一起熬汤,喝完明日,就没啥事了。散了吧!”众人千恩万谢,这一次的祠堂聚会,比起昨夜间的死气沉沉,嘈杂了不少,乡民们不比昨日连喘气都乏力,今日一天,人们的气色就完全不同了。
郝生印在宗祠薄上记录:“光绪二十六年,大旱大疫,郝玉元赴府谷寻药,以鸦片为药引,立效!活族人无数。”
雪后初晴,正是庄稼收割的季节,这一年荞麦的收成尚可,庄上的人们又一次摆脱了天灾和瘟疫主导下的“老天爷收人”的命运。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