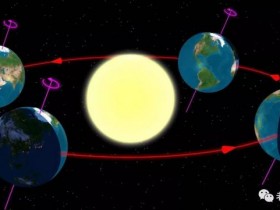民人们都去川里修粮仓去了,没有乐人,也没有太多闹婚的人,在孤清和苍凉中,郝玉元将魏氏娶进家门。魏氏少言寡语,除了做饭收拾家务,其他事情上却缺少其兄长的精明。郝玉元对此早有耳闻,况且魏先生有言在先,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一个能招呼家务的人,也就顶满足了。
魏氏对两个娃娃表现出了极大地爱护,这大约是出于母性的本能。郝玉元见此,更加尊敬魏氏。
收完最后一料庄稼,除去交给官家的粮款,基本上没有多少盈余。原本相安无事,然而祸从中来,郝玉元在塬上的房屋,却被修建粮仓的官吏们看中了。郝玉元将将把口粮收拾干净,这些官老爷们带着兵丁就进驻了郝家大宅。官命难违,郝玉元只好将一家老小送到玉珍家里安置,顺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准备外出开始新的生活。
关于去向,郝玉元经过了各种考虑,最终都没有定弦。然而,所有迁徙地点,并不包括当时的热点包头以及沙圪堵等地。郝玉秀得知后问道:“哥,咱不去口外了?”郝玉元道:“我听说口外如今钱粮也重,咱得找一个避开清家的所在。”玉秀问:“那咱去哪儿?”郝玉元道:“刮宁夏!”
郝玉珍道:“不是说投奔我正道叔嘛?”郝玉元说:“郝正道都死了。我倒听算卦的瞎子说,正道不是病死的,是在内蒙割洋烟半路让劫道的抢了,连打带诈坐下病了,后来连病带气死了的。我说到口外这条道上也不安宁。咱还不如沿着长城就往西走,人家走西口,咱就刮宁夏!(榆林人走西口是北上到乌审旗、鄂托克、乌海市(过黄河)、杭锦后旗(后大套)。榆林南六县走西口大部分人纳入榆林人北上再西渡黄河之路线。另一部分人则纳入西三县之路线。西三县包括横山、靖边、定边县。他们的路线是沿长城出定边进入盐池(宁夏)、灵武(渡黄河)、银川、吴忠,再北上进入银川平原。所以西三县人走西口又叫“走西头”“刮宁夏”)左宗棠把乱匪撵走了,那边土地广阔,有的是田地。”弟兄三个商量了几回,这事情就定下来了。
光绪三十三年春,罕见的大风沙袭击了整个西北,对面见不着人,整个府谷县在一片苍凉中迎来了所谓的春天,树上一片叶子都没有。郝家用于走西口的家当已经准备停当,日子也看好了。那是郝玉元让后梁上的瞎子给看得日子,玉珍听闻笑了:“哥,那瞎子啥都看不见,你指望他能给你挑个好日子?”郝玉元却对此深信不疑,道:“瞎子看不见世间的人事,却能看见世间看不见的人事,这事情我有主张,你不用管。”
三月十八这一天大早,少有的不刮风而没有风沙的天气。郝玉珍啧啧称奇:“这瞎子还真有些门道。他没说让咱往哪儿走能安身立命?”郝玉元道:“随着古长城朝西走!”郝玉元、郝玉珍、郝玉秀弟兄三人,带着家里的一匹白马,一头骆驼,拉着炭、麻绳、水烟、布匹、棉花、铁器、农具,趁着天微明的时刻,带上一家子老小甚至长工就出门了。
走到半梁上,郝玉元弟兄三个才看到几户近门的本家已经等候多时了,大小十几口鼓鼓囊囊携着抱着,一看就是逃难的光景。郝玉元见状,脸上一阵抽搐,良久才道:“走!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这一回了!”众人也都默默地跟在郝玉元的后面,朝着未知的未来缓缓地行进着。
走了大半日,见那一轮红日渐渐坠下远处的山峦,一大家子方才走到了官道上,远处的长城就在眼前,然而望山跑死马,这一段路,谁晓得要走多长时间。官道上人流车马鼎沸,大队走西口的人马沿长城一线往西部迁徙前行。其中一个黑脸大汉,带着十几头骆驼,慢慢前行,一看那肤色和走路不慌不忙的样子,就是经常出入口外的人。
玉珍前去问路:“乡邻,咱们逃荒,先去哪里?”这个人道:“这也不晓得,逃什么荒?你们怕是逃乱荒的?”玉珍笑道:“可不是逃乱荒嘛!”这人笑:“哎呀,逃乱荒怕是不好安顿生计吧?有个落脚地没有?”玉珍道:“刮宁夏嘛!”那人道:“刮宁夏人也不少,沿长城下靖边,过定边下盐池、到中卫银川,一路上要艰难些。还不如去蒙古,五十里一个大车店,沿路都有咱府谷乡党照应。路上也安生,经管好牲灵,倒也没甚事。”玉珍心灰意冷地回来了,原本就对刮宁夏不太感冒的玉珍此时找到了发泄的缘由。玉秀却道:“你不信咱哥,倒信一个生人。”玉珍道:“咱哥也没出来过,你看刚才那个人,一看就是跑家子。咱得打问打问,走错了就完了。”郝玉元道:“一路多打问是对的,路上都多长个心眼,我听人说这路上劫道的土匪多。”郝玉元却绝不提去口外的事。
一路无话,眼看天黑下来,一个浑厚而粗壮的声音唱起来:“大摇大摆大路上来,你把你那白个脸脸掉过来,摇三摆……”这一声信天游让队伍里的所有人精神一振,也有嗓门好的就对上了。一时间,“花儿”四起,那酸楚而又开放、让人心跳脸红而又充满悲凉的花儿,把逃难路上人们的困顿都抖落了。
在黑脸人的带领下,一帮人才住进了驿站里。这一路行来,如果没有驿站,无论谁有天大的能耐,也走不出这满布的风沙。
住店并非是免费的。郝玉元为了不把钱财外露,就打算用羊皮跟管事儿的打点,不想管事儿的一听是羊皮,二话不说就约定了价格。原来,在这一带行走,货物永远比银钱更紧俏。
刚刚交割完毕,那黑脸就道:“你没有银洋?”郝玉元:“没有多少,原本就是下苦种地挡羊的,皮子多得是,银钱不曾有。”那黑脸道:“一看你就是没出过门。在这地界,银钱能花出去就花,东西留下才是正经。这羊皮冷了能穿戴,饿了能果腹,咋能打点住店哩!”郝玉元听完又不胜后悔,但是说出去的话、做下的事,犹如泼出去的水,怎么好收回呢?
那黑脸探口气道:“以后有甚事,听我的安排。”郝玉元这才认真地看了一眼这黑脸,道:“我瞅着你面熟!”黑脸笑笑:“我是魏先生店里改改的大哥!你原先是我兄弟的东家。”郝玉元这才笑道:“你是迎弟!”黑脸也不好意思地笑了:“魏先生担心一路上不安生,正好我要下定边,一路上就捎带把你们送到。怕你们不悦意,也就没有敢声张。”周边郝玉元的乡亲近门闻此,原本已经打算退却的人,此时也有了心劲了。
这是一间大屋子,里面两张大炕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男人睡一堵炕,女人睡在另一张炕上。炕上面铺着稻草,稻草上面是又黑又臭的褥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棉絮和羊毛都快漏完了,几乎只剩下薄薄两层皮。中间是一条过道,有木质的水桶,刚刚打满的一桶热水,供全屋子的人洗脚,女人们都不乐意在众人面前露出小脚,只有男人们不在意,纷纷洗了脚睡下。
窗外的尚比较圆的月亮带着光晕把亮光通过窗棱投射进来。此时,他们完全没有离开家乡的兴奋,尽管那个家乡在黄土高原上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山峁,却是他们非常想念的曾经的家的所在。忙碌了一天,总算能歇下了,很多娃娃却在此时哭了起来:“我想回家!”这一哭,队伍里的七八个娃娃就哭乱杆了,惹得眼浅的女人们也眼圈红红的。
其他客人有不乐意的就喊:“嚎甚哩!将将睡下就嚎丧!”转脸一想不对,这不是咒自己死呢,于是就又吐了两口。
一夜无事。第二日天将亮的时候,众人们都开始准备一天的干粮和路上的水了。郝玉元鉴于上次的经验,用银钱换了干粮和清水,那伙计见银钱拿出来,有些疑惑,好在也没有多为难他们,都给他们备好了。
人和牲灵经过一夜的休整,精力得到补充,趁着东方将白,众人在迎弟的带领下,赶着牲灵和板车,沿着长城栈道,一路朝西慢慢行进了。
太阳出来之后不久,风沙就起来了。这次风沙特别大,对面看不着人。迎弟带着众人把骆驼放在前面,骡马放在后面,摆成一条长队。妇女和娃娃们放在驼队的后面,阻挡一些风沙。其他的壮劳力则站在前面牵骆驼。
风沙持续地肆虐,打在人的脸上生疼。这支队伍走得更慢了,路上陆续有逃荒的人口体力不支倒地,后面的人也有被尸体绊倒的,随后,尸体身上的衣服和所有物品就被一抢而空。

郝玉元见此,就跟迎弟商量:“不行找个避风的地方,避一避再走。大人我看还罢了,娃娃们怕是受不下这罪。”迎弟看着魏氏将两个小娃娃窝在怀里,点了点头,喊了一声:“都跟我走!前面有个烽火台,进去避一避!”
众人这才朝着一个鼓起的山包一样的烽火台走去。等到了跟前,里面全是逃荒的难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迎弟只好带着驼队马匹和众人,在这山包的避风处安顿,避风处也是一群难民,仍然难以落脚,不过好歹有个风沙稍微小一点的地方了。郝玉元招呼大家吃了些干粮,喝了些水。休整了一阵,眼见一片太阳暗淡下去了,风沙停住了,正准备离开,一个声音在人群中响起:“前面一只肥羊!”众人朝着人群中看去,又听迎弟大喊:“爷长着俩瘦角!”那人就再不言语了。
等着郝玉元等重新走上管道,远处的雷电哗啦哗啦闪着,这才问迎弟:“刚才那人喊得是啥意思?”迎弟道:“那是胡子和土匪的暗语。是试探咱们这帮子人有没有道上人照看。如果答不上来后一句话,咱们这些东西就都归了他们了。在这一带混饭的人,都知道这规矩。不过这二年不比往年,有时候胡子也找熟人下手,毕竟这生计太艰难了。咱也不能掉以轻心。”
连续走了两天,众人这才走到神木境内,照这进度再往前走还得十几天的时间。郝玉元心里不免担忧: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会遇到甚事情。粮食和清水已经缩减到最极限了。装水的羊皮眼见得到底了。玉珍这时候喊了一声:“前头有一口井!”众人一眼望去,果然是一口官井,可是到了跟前,里面全是黄沙,连一滴水都没有。
每个人的嘴唇周围都起了一层黑皮,缺水已经影响这支逃难队伍的行进速度。没有水是绝对不行的,可在这长城脚下的荒漠里,经历了长达十几个月的干旱之后,哪里还有水可用?郝玉元道:“在这里等也是送死,不如继续往西走!走着寻水!”众人无奈之下,也只能跟着走。迎弟不知道从哪儿摘了一些酸枣和沙果,分给了娃娃们,大家这才重新上路。
到了夜间,众人就让牲口围着,睡在里面。迎弟把铁锅、陶罐放在树跟前,有的直接挂在树梢上,到了天亮再取下来,汇聚起来有一半壶水,却也是杯水车薪,不过聊胜于无,第二天晚上,众人就都学会了这办法,早上起来却发现瓦罐和铁锅都不见了。
到了靖边城,这支已经筋疲力尽的逃荒队伍,总算吃了一口热乎饭,补充了些水和干粮。这时候,负重进一步减少,银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而随着水价的攀升,羊皮也换掉了大半。
让郝玉元心里感到欣慰的是,相比较于一路上见到的死在路上、病在路上、伤在路上的众多乡亲,跟他一起逃出来的这些近门的宗族们,没有一个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掉队,更没有疾病和受伤,更幸运的是遇到了迎弟带路,一路上也没有被胡子抢劫。
进入靖边地界之后,长城沿线的人明显少了起来。风沙小了,天空阴沉沉的,几点雨滴不住地落下来。路上一个半大的孩子捧着一个破碗嚎啕大哭,郝玉元不忍,就要前去救助,却被迎弟一把抓住:“一路上这事情多了,你能救过来几个?这世道能顾好自己就是积德行善!”
郝玉元吃惊地望着冷静得可怕的迎弟,挣脱了他的手,去把那孩子抱起来,放到了魏氏跟前。魏氏对此毫无表情,把那孩子的破碗扔掉,用手里的一个梳子给他梳头。
迎弟叹了口气,道:“咱们离宁夏还有一段距离,我知道老东家心善,为了咱能活命,就这一回?能行不?”郝玉元看着迎弟,心情非常复杂,常年的奔波在外,让迎弟见过了太多的人间惨剧。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哲学:“先管好自己,就是积德行善!”这不能怪他,人在极端的环境下,一定会先自我保护,追求自我生存。
郝玉元看着迎弟道:“能成!我再也不管了,就这一回。”迎弟点点头,拍了拍郝玉元的胳膊牵了骆驼继续前行了。
果不其然!一路上这类丢弃孩子的情景非常常见,郝玉元拦住一对将要丢弃孩子的父母:“好好的娃!为甚就丢在这路上!”那夫妇看着郝玉元道:“大人都养不活,还顾得上娃娃?”那女人道:“我们现在自己逃荒都不能自保,等将来在其他地方生住了,还能再生养,现时也只能是这样了。”
那对夫妇嘴唇干涸,一脸风沙,根本看不出年龄来,郝玉元听闻,只能默默放开双手,任凭对方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处理子女。迎弟道:“老东家,你这一路上见到的世事还没有经见够?宁做太平犬,不当乱世人。现如今的世道就是这样子,民人们能有一口吃的,任谁也不会拖家带口,一路上遭灾逢难、生死未卜地逃荒。”郝玉元脸色阴沉:“我再见不得这号事情了,我只求安安生生地到了宁夏,安顿下来这一大家子。”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郝玉元带着一大家子进入了定边城。这是接近宁夏府的一座商业繁华的边塞城池,县城里除了做买卖的各地盐商之外,就是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游民和清家的散兵游勇。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对这些人口进行划分的话,那就是要饭的和吃粮的。
迎弟和郝玉元找遍了整个县城,也没有一个得空的落脚的地方。折腾了半天,终于在城南四五里处找到了一座庙,那庙里的住持也是府谷人,念在同乡的情分,在大风天收留了这样一大家子人。寺庙不大,只有十几个僧人,住持双手合十道:“兵荒马乱的,庙里也香火禁绝,少有施主布施。好在后园有一口甜水井,每日前来打水的人给些许粮食糊口,怠慢各位了!阿弥陀佛。”郝玉元和迎弟还礼感谢。郝玉元把自家带着的粮食给了庙里些许,那方住持立即拜倒感谢,吩咐僧众打柴生火,做些米粥给众人。
郝玉元等人在这座山庙中住了小半个月,等着风沙停了,这才收拾所带物件拜别了住持准备离去。而住持却道:“施主稍等。”随后拿出来几个纸包,道:“这是先祖留下的药粉,民人逃难中惹上的病症都能治疗,施主是乐善好施之人,必有福报,这几包药给施主带去,以防万一。”郝玉元携众人再谢,告辞而去。
迎弟已经到达定边,这边的买卖也要开始了,就和郝玉元告别而去,临走要送一头骆驼给郝玉元,而郝玉元百般推辞:“你是买卖人,常年走这条道,没有骆驼怎么能行?这万万使不得!”迎弟这才不太放心道:“剩下的路程虽然不远了,但是更要小心。你们先去盐湖做些营生,那地方饿不到人,随后再找落脚的地方。”郝玉元听闻觉得言之有理,自古盐场都是商业富庶之地,去那里找营生,实在是一个简洁快当的办法。
这一大家子人按照迎弟提供的路线,就朝着盐湖前行了。谁料到,走到半道,那个拾下的娃娃浑身发热打摆子、牙关紧咬,已经不省人事了!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