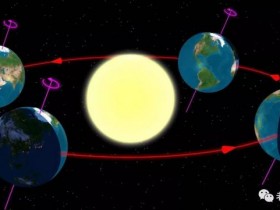郝玉元见状,立即掐那娃娃的人中,郝玉秀在一旁喊:“鼓劲掐!不敢让娃把舌头咬了!”那娃娃被掐了人中之后渐渐缓过神来,微微睁开眼睛,只见他干涸皴裂的嘴唇动了动:“叔……我不行了,你把我……随手撩了……算了……”郝玉元豆大的泪珠子跌落下来,掉在了这娃娃的嘴唇上,那娃娃抿了抿嘴唇,说了一个字:“苦!”就又一次晕厥了。
郝玉林道:“把老和尚给的药试火一下。”郝玉元听闻,立即拿出那一包药,接了一碗水调和了,给这娃娃服下去,安顿他在马车的一个角落的破羊毛堆里睡下了。
“生死就看你娃的造化了。”郝玉元心里想着,赶着马车朝着盐湖走去,身后一大家子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
走了半晌,玉秀上前打问了当地人,才知晓盐湖在与盐池交界的地方,还有一百多里地,照他们目前的速度,恐怕还得走两天。
郝玉元弟兄三个只好安顿大家在城外露宿,因为他们根本住不起县城的驿馆。定边县城与其他县城相比,非常繁华,店铺林立,商旅众多,这也催生了当地的驿馆价格高昂。郝玉元从府谷带来的银钱早在进入靖边的时候就全部换成了粮食和水。如今只剩下半日的嚼谷,能不能撑到盐湖都不一定。
众人稍微吃了些东西,这才把几口牲口围起来,人在里面睡下。睡到半夜,那捡来的娃娃惊叫起来,众人连忙坐起。只见几个黑影窜远了。郝玉元大惊:“完了!遭贼了!”立即起身检查物件。而那贼人们遇到惊动,早都跑远了,郝玉秀火爆脾气,翻身上马就准备去追,郝玉元见没有少什么东西,这才一把拉住马头:“算了,咱们是客户,人生地不熟的,不要惹事。”
郝玉秀瞪大了眼睛,道:“我抓住狗日的,非把狗日的打个半死。”郝玉林也跟着苦劝,玉秀这才作罢。经过这一折腾,众人也没有了睡意。郝玉元从周边的黄沙中找来些干裂的树根和树干,点起了火,几个人围在火堆说着话。
郝玉秀说:“这娃娃看似好了。”郝玉元看了看坐在一旁的那个捡来的瘦小的娃娃:“你好些了?”那孩子点了点头,还是很衰弱的样子。郝玉元问:“你叫甚名字?哪里生的?”那娃娃道:“我叫二怪,家在神木府城南王家塔村,全村人都逃难出来了,就剩下我一个单蹦了,其他的都死了。”郝玉元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家乡就在几百里外的山峁里,也是能够挡羊种粮的好地方,如今却不得不外出寻找活路,这种粮的人甚年代才能不受这罪?才能安安生生地过日月?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整个南梁最有学问的郝正民都回答不了,还有谁能给出答案?好在路上捡了个二怪,也算是把这一家子唯一的根苗救下来了。而郝玉元这一家子近门的宗人一个不少地走出来了。当官的吃粮的,就算再折腾,也跟他没有关系了,那几间曾经傲立南梁几十年的青砖大瓦房,如今就算一把火烧了,也跟他没有关系了。唯一难以割舍的是老爹的坟茔还孤零零地守着南梁,妻子的坟茔也孤零零在北壕里一个背风的地界鼓起着一抔黄土。
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都开始了,生而复死,死而复生,这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不断轮回着的。即将要开始的新的生活,真的就那么美好吗?就一定能哄饱肚子吗?现时看来,这事情还真不好说,先安顿下来再说吧。胡思乱想了一阵,郝玉元自己的脑袋也乱了。他把珍藏的烟叶拿了出来,跟玉林和玉秀分了些,抽了一阵子,天还没有亮的意思,三个人这才轮流又睡了一阵。
天大亮的时候,这支队伍已经沿着长城朝着西南方向继续行走了。他们要去一个被称作“花马池”的地方,那里是西北盐业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常年缺人,而最紧缺的无疑是盐工。
郝玉元道:“今日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花马池,要是再续不上粮食,咱就等着刨坑埋人吧。”
这样一支穿着破破烂烂、饱经风霜的逃荒队伍,脸上被风沙吹打得已经看不见原本的面容,却充满着求生的欲望,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心里都鼓着一股劲,那就是对生活的希望,对生命的憧憬。打马前行,一望无尽的风沙并没有淡去的意思。
花马池是定边四大盐州之一,盐业是盐池、定边乃至靖边的民人们生活的命脉之所在,更是官府干涉最多的行业,其中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历朝历代,食盐为官方提供着最稳定的税收来源。
郝玉元用仅有的十张羊皮寻了个荐头,荐头答应第二天带他们去干活。当天夜里,这一大家子人就在盐湖附近的一个开阔地露宿。
第二天一早,那荐头果然来了,众人都很兴奋。荐头把工号分发给每个壮劳力,随后就领着他们去盐湖打盐。二怪缠着荐头执意要去,那荐头听二怪口音与他人不同,就问二怪是哪哒人。二怪道:“我是榆林府王家塔的,半路上被元叔拾下的。”那荐头听闻,扔下三张羊皮给郝玉元:“我看你是个忠诚老实的人,这几张羊皮算是谢呈你救我的乡人。”转头又对二怪说:“有种!半大小子不吃闲饭,明儿上盐场打盐!”
“南风至,风起波生,即水凝盐。”初夏时节,温热的南风远涉万里,来到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盐湖,原本平静的湖水被春风吹皱,随风翻卷,浪花在风中迅速凝结,生成闪闪发光的盐晶。盐湖周边白茫茫一片,结晶的盐粒如同积雪一样,蔚为壮观。
盐湖周边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咸味以及卤水特殊的气味。盐工们大多衣着破烂,加上初夏季节,每个人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远近各处起着一个个大小不一且形状甚不规则的盐堆。

郝玉元带来的亲近族人大多算得上是村里的精英,个个都是种地干活的好手。对于如此简单而不必费力的工作,哪须半天便熟悉了所有的流程。在盐头的带领下,众人很快分到了工具。在烈日下,众人在盐湖边上任意挥洒着自己的汗水。中午一顿饭由专人送到盐场,咸菜和白面馒头尽饱吃,甚至还有腌肉这样难得的吃食。
众人抡圆了肚子吃了个饱,二怪却趁人不注意往身上藏了俩馍馍,被荐头看见一脚踢得趴在地上:“只能吃不能拿,这规矩你家大人没给你说过!”郝玉元立即扔下饭碗跑过来抱住二怪:“你这人,早起还好好的,今儿咋就变了个人,真心狠的?”荐头道:“这是教他懂规矩,不打他记不住!父母不在了,这娃娃更不能惯!”说完扭头就走了。二怪哭道:“我就想给生贵和二妞带个馍馍……”郝玉元感动了,荐头又转头道:“你们吃啥屋里人就吃啥,饿不着他们。这里不缺粮食!”
盐湖每年的农历五六月份是产盐的旺季,却也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郝玉元带着族人们到达花马池的时间,正好一年中的打盐季。因为舍得出苦力,族人们完成的定量总是这场子里最多的,荐头脸上也有光彩,于是暗地里给他们分配些好的活路——出力不必多,利润也丰厚。
几个月下来,所有人都一扫逃荒路上的颓唐,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恢复如初,不仅衣食无忧,手头也有了些银钱和粮食。甚至连二怪的个头也窜出一大截子。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储备,他们才得以度过之后的危机。
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七月初一,郝玉元把元宝、纸钞之类的东西,朝着故乡的方向烧给老父亲的时候,荐头匆匆忙忙地带来了又一次改变逃荒者命运的消息。那荐头气喘吁吁道:“快跑!带着一家老小快跑!盐场被三边的勇字营盯上了,见人就杀!谁都活不了!”郝玉元听闻顾不上吃惊,立即带着族人牵着牲口趁夜赶路。
没有方向,郝玉元不愿意放弃盐湖这样的生存之地,他心里有个想法:即使逃命也不能离开盐湖太远,以后迟早要回来,这碗饭比起在田里刨食管用多了。
临走前,郝玉元问过荐头:“咱们实实在在下苦力谋食,咋能惹上地方团练哩?”那荐头道:“这些盐湖本身就是官员的钱篓子,今天这个干,明天那个干,谁给钱多这活路就给谁。怕是这回咱们的盐头儿钱没给够,被其他人顶了,当官的也不好说叫人就走,盐头儿都有些自己的势力,加上这么多工人,要是闹事谁都受不了。官家干脆以匪打击,直接剿灭了事。这就是这里的王法。毕竟死几个人不算啥,老钱才是官府的主业!”
郝玉元在干活的时候专门留意了一些游走在盐湖边缘的人——盐贩子。这些人无论是哪个字号打盐,也不影响生意,尽管盐贩子赚得不多,养家糊口却是不难。所以,郝玉元打算以盐湖为中心生活,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他心里依然有一股劲儿,即使不能恢复当年在南梁的风光家业,至少也应该不为人后。
这一大家子在天亮之后到了宁夏府盐池县,郝玉元见这里山势平缓,天青地阔,不禁心情大好。郝玉秀问:“哥,咱到这里咋谋生计?”郝玉元笑道:“你看这么大的地界,还养活不了咱这一大家子?”
信马由缰,众人拖家带口来到一座寺庙跟前,庙门上写着“灵应寺”三个大字,众人进入庙门,在大殿外面的空地上坐下歇息。正说话间,来了两个年轻僧人,合掌问询:“几位菩萨是从甚宝地来的?”郝玉元行礼,简略说了逃难经历,那僧人便道:“路上可曾遇到寺庙?”郝玉元道:“定边县安寺庙见过一个老住持,俗家是府谷人,叨扰过几日,还承蒙赐药,救了我等众人一命。”那僧人闻此道:“这就对了,那住持法号正远,是我的师兄。我法号就是惠远。”于是吩咐僧人看茶持斋,郝玉元不敢怠慢,忙把自带的粮食拿出一部分交给惠远,那僧人合掌谢了。
在寺庙里面住了几日,惠远大和尚照顾如常。郝玉元却不忍多扰准备告辞。惠远问:“这一走准备到哪儿去?”郝玉元道:“还不知晓。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倒是我爷爷私塾里教过一个学生,中了科举在这里做官,后人安插在这里。原本姓宋,如今也不知道家在何处。”惠远说:“这地方土地宽广,回乱的时候民人死伤甚多。养活一大家子倒是不难。就是官家见不得人多,这里的民人也大多从东路来,怕是容不得这么大的家族,你们化整为零,各自寻些生路,倒是比一大家族一起奔忙要好些。”
郝玉元听闻之后,心下就明白了:这地方规矩多,民人不能聚集只怕是最大的规矩,在盐场算是见识了这样的教训。除了盐头没有行贿合适之外,当官的见不得民人们长期聚在一处地方也是诱因,盐头一旦形成势利,后果不用赘述,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强行驱离,也是基于同治回乱的教训。
惠远又道:“你们随便找些地界就能熬活挣口饭吃,这地方生存倒是不难。”郝玉元于是跟弟兄们分手,将一堆家业分了,自己分得一匹白马、两担子行李。准备走的时候,惠远又说:“二怪这娃有慧根,我寺庙里又正好缺人,你要是不见怪,把这娃娃也留下吧?”郝玉元问二怪:“叔现时也自顾不过来,你要跟我熬活下苦,我也能养活你,你要愿意留下,这惠远师傅也是善人,跟他也不至于受苦。你看?”二怪眼里流泪,不忍回答,想了半晌,道:“元叔,你以后多来看我。”就转身跑进庙里了。
郝玉元诸多不舍,却也算是给二怪找了个安身立命之处,于是收起分别的念想,牵着马匹,驮着行李,领着魏氏和一儿一女,与惠远、二怪以及玉林、玉秀等族人分别。
这里果然地广人稀,郝玉元一家一路上没有遇到几个人,天将黑的时候,才终于到了一个村子,这村子其实与南梁并无太大不同,都是一大片土塬上零星住着几户人家。有一户人家的房屋修建得稍稍完整些,郝玉元便策马前行,到了那家门口,恰逢那家主出来,那人见了郝玉元立即对屋里道:“盛些饭食!招呼一下这苦焦的乡邻。”随后将郝玉元一家子让进屋里。
这院子里面是十几孔窑洞,都掏在一个十几米高的壕壁上,用青砖箍了门边,一看就是家境殷实的主家。主人将郝玉元的白马拴在院子角落的一处草棚底下石槽里面有铡刀切碎的荞麦杆,荞麦干油大,正是骡马最好的饲料。
郝玉元一家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终于吃上了地道的盐池荞面。吃饱饭之后,那主人开口打问:“听口音你不是这附近庄上的?”郝玉元如实回答,那人道:“咱这庄子叫罗渠,姓罗的是庄户。我家姓饶,也是外来户。不过这二年我家族人多了,也置了些地,有了些产业。”郝玉元道:“咱庄户上有没有雇‘长在’跟‘日子’的(长在,当地人对长工的称呼;日子,当地人对短工的称呼)?”饶家道:“这里地土宽,要说雇人,家家都得雇人,顾不过来种嘛!但雇人却雇不过三年。”郝玉元有些疑惑地问:“那是为甚?”饶家道:“雇工干不过三年,攒下银钱就找一个没人的山峁开荒种地,挡羊剥皮,掏了窑洞就自立门户过日月去了。故而长在不多见,日子倒有,现时不是农忙时节,雇日子的人少。你怕是不好寻。”
郝玉元叹了一口气道:“原本以为到这里能混个肚子圆,不想找个吃饭的营生这么艰难。”饶家却道:“倒也不用熬煎,这事情好说。你先在我这里住着,一应吃住用度都不用你管,干够三年,随你顶门立户,我这里给你牛羊和钱粮。”郝玉元一听立即答应。
这是一个机会!一次重生的机会,一次能够在这个地方落脚的机会,更是一个能够再次东山再起、把郝氏家族在另一个地方开枝散叶、发扬光大的绝好机会。
郝玉元与罗渠饶家的东家签订了三年的合同,吃穿用度由东家供给,每年帮助东家耕地下种、锄地、经管、收割,一年到头勤勤恳恳,为人谨慎老实,也从不多话。郝玉元是干活的把式,力气又是不惜的,在田地里驾辕犁地倒比罗渠村最好的经管牲口的人还要干得好,这让饶家人对郝玉元非常满意。
第二年的春播时节,郝玉元早早就把主家的地犁毕种完了。这时候,罗渠饶家的窑洞院落门前人都围严了,都要让郝玉元去帮忙犁地。饶氏主家大度地说:“郝相你只管去,咱家的地犁毕了,没有啥紧活路,你挣得钱粮全部归你,我一分不要,骡马家具你随便使唤,我连一句话都没有。”郝玉元感激着主家的恩惠,眼睛一热,起身牵着白马出门了。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