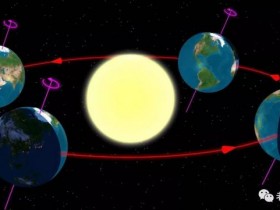郝玉元牵着骡马在山梁间的地头忙碌的时候,周边围着不少的农人,他们惊奇于郝玉元改造后的犁铧——吃土深却又省时省力。郝玉元早都发现当地的犁铧与老家的不同,而土质又相差不大——盐池的地沙土稍多些。因此,他结合当地的沙土土质大胆地将当地的犁铧进行了改造,没想到这一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郝玉元熬活的东家饶忠厚算得上罗渠村顶忠厚仁义的主家了。郝玉元侍候庄稼应心尽力,改造犁铧不仅提高了耕作效率,更让饶忠厚家的粮食比往年多收了三四成。饶忠厚高兴道:“郝相一看就是经管庄稼的把式!今年多打的粮食,你全部装回去!该粜了换钱哩,该自己攒哩,全部都由你!”郝玉元惊道:“这几万斤的粮食我可不敢要。谁请长在花这么大的工价?”
饶忠厚笑道:“郝相你差了。我原本地里该打多少粮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每一年差不到千数斤。年景好了多打一两千斤,年景不好了少打五六千。今年年景不好,一样的地多打了这么多粮食,全部给你我也不吃亏,全当我不花钱不出粮雇了个长在。我能吃啥亏?哪哒来的工价?”
郝玉元语言短些,平日里不甚多说话,如今听忠厚这么说,心里的感激自不用说,他狠命地抽了一口烟,粗大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这才道:“好嘛!我听你的。”
更让饶忠厚感到不吃亏的是自家的二百多只羊,在郝玉元的精心经管下已经超过三百头,几十只羊崽子跟着母羊在自家的山头上撒欢跑着,不似往年病病殃殃的样子。这让饶忠厚在村里人面前更加得意,走路说话的底气都足了。附近庄上的人都说:“忠厚请了个好长在,日子过得受活得不像啥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郝玉元在罗渠积攒着钱粮、准备在这里扎根的时候,郝玉秀却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抉择。他误打误撞进入花马池营面对成队列的官兵倒没有感到任何胆怯,他从小就以胆大出名。这些吃粮的粮子在他看来,无非就是人多势众,欺负百姓的恶人而已。
直到把着营门的官兵呵斥:“弄啥的!”郝玉秀才懒洋洋道:“逃荒的!”官兵冷笑道:“把你个刁民!逃荒也不看地方!寻得挨打哩!”郝玉秀却不恼:“逃荒的把多半条命都撂到半路上了,还在乎这是甚地方!”官兵一听这话,反而觉得这个逃荒的并不简单,究竟哪里不简单却又说不上来。在那个年代,灾民看见官兵都吓得躲到一边去了,这个逃荒的却不卑不亢,连一点畏惧都没有。
这兵勇反倒有些怯了。他进去了一会儿,出来就成了两个人,前面走着的是个穿着官服的小头目:“你到底是弄啥的?”郝玉秀道:“都说了逃荒的。”小头目道:“你不像逃荒的。”郝玉秀笑道:“逃荒的还用冒充?又不是甚长脸的事。”那头目更加怀疑,吩咐众人将郝玉秀带到了兵营里。
郝玉秀带着两个儿子,一家三口进了兵营。头目给郝玉秀拿来饭食,这一家子抡起膀子美美吃了一回。郝玉秀想:就算要杀头,也得吃饱喝足了再说。
头目见他们吃饱喝足,这才道:“我见你不是俗人,可念过书?”郝玉秀道:“念过。光绪二十九年神木一等第五名补廪膳生。”那军官道:“哟!我说不一般,果然是个秀才,顶有文墨的人!稀罕稀罕!”军官说完让人拿来文房四宝,现场让郝玉秀写上一张募兵告示。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哪须一时三刻,郝玉秀一气呵成,那字体苍劲有力,力透纸背。军官看后大加赞叹:“且不说这文采如何,就这一笔好字,任谁看了都不得不佩服!你不要逃荒了,就留在我这军营里。”郝玉秀心想: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今这秀才却进了军营了!看来这人生百态,世事无常,所言不虚呵!
宁夏府名为府,却是一个准省级编制,清廷掌管宁夏军务的是宁夏提督。庚子拳变之后,清廷建立新军,在甘肃驻军的为甘肃混成协,如今驻扎在花马池的正是清廷新军的一个营。其中营部51人,辖3队525人,计576人。内有炮18门,骡马260匹。
郝玉秀得了个吃饭的营生,却完全高兴不起来。自从朝廷废了科举之后,秀才的功名完全没有了用处,他对于兵营是完全陌生的,家乡的兵勇们各个面目可憎,又增添了他对兵营的恐惧。
大概是长期缺乏文职,兵营中的各种文书和公文堆积如山,而文书所在的营房已经好久没有了人气,连锁子都锈实了。郝玉秀正襟危坐,一个人在偌大的公文房中办公,两个娃娃就在一旁玩耍嬉闹。郝玉秀把未完成的公文放在案牍的左侧,完成的就在右侧整整齐齐地摆放好。仅仅一上午工夫,最紧要的公文都已经处理完毕,着人加急送到银川的宁夏提督府。
不几日,一份嘉奖令和军需奖励便告到位,营管带大喜,在营区内设宴席,正式接纳郝玉秀成为新军的一员。在废除科举之后,秀才已经再无可能投身仕途,只能通过募兵参军一条路养家糊口。况且新军粮饷丰厚,又绝少缺饷之事。因此秀才进军营往往趋之若鹜。西北一带因地广人稀,加上战乱影响,民人稀少,因此少有通文墨者,郝玉秀在这里算是如鱼得水。
区区半年时间,郝玉秀就彻底熟悉了营区的所有事项,加上他为人谨慎,勤恳忠厚又实诚,更加得到管带的器重,不断升职,后来竟在定边花马池一处地方置了宅子,立了家业。而郝玉林自从离开灵应寺之后,对于未来也是不得要领。他一路向西,不知去向。尽管郝玉秀派人多方打听,却毫无下落。
到了第二年盐花开的日子,营里接到事务,要带兵剿灭盐池附近的乱民。郝玉秀立即随军前往,两个儿子则交给伙夫照看。
到了盐湖之后,整个盐湖周边早都打乱杆了。这些被称作乱民的人衣衫褴褛,郝玉秀对他们绝不陌生——这些人与一年前在这里熬活下苦的自己并无不同。他们用手中简单的工具与当地的勇字营大打出手,勇字营很少有枪,都是冷兵器,即便如此,这些所谓的乱民也被砍杀无数,原本白花花的盐湖蒙上了一层浓重的血色。
这些衣衫褴褛的盐农不断涌上来,勇字营也死伤不少,眼看不敌,郝玉秀的新军营正好赶到,新军用的新式武器,一排枪放过去,那些乱民被打死打散,众人被枪声震慑一阵,随即四散逃命。勇字营分头包围,却也不得要领,只抓住很小一部分。
这些被抓的人里面,竟然也有衣着光鲜的人。其中包括郝玉秀原来的荐头。郝玉秀单独将荐头提出来,问:“你咋闹得?”那荐头见了郝玉秀,原本死灰一样的脸上放出求生的光芒:“郝相,快救我!救我!容后面我给你详说。”
郝玉秀禀告了管带,说这人是自家亲戚,有心救下。那管带见了荐头,就对勇字营的千总道:“梁千总,这个人我带回新军营了。”那千总对新军原本就低头哈腰,此时就是有任何要求也不敢不从,立即应允。郝玉秀这才将荐头带回花马池兵营中。
到了兵营那荐头才道:“我本家姓郑,陕西安康人。我从光绪十九年就来到花马池盐湖,做盐的买卖十几年了,内里的所有事情我比自己的掌纹还熟悉。今年盐头给了官家六千多两银子,已经开始打盐了,另一个盐头给了六千五百两。这边当然不干,于是就闹事,官家就叫人剿灭。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郝玉秀道:“如今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以后何以为继?我看周边百姓守着盐湖都吃不上盐,还有人熬土晒盐,这盐湖是该管了。”管带道:“希文(郝玉秀字希文)你是这,给陕西总督递一份折子,就把盐湖的事情说清就行。上回陕西总督升允就说起这盐湖的事情,你这份折子比干滩拉船要好得多。郑相知道得又多。只要咱新军能把盐湖把住,以后咱西北的边境可保无忧。”郝玉秀听闻,欣然应允。
这一夜,郝玉秀的营帐里面灯火彻夜未熄,第二日,一份文不加点的长折子就由兵勇快马送往西安满城升允的驻地去了。
新军屯兵花马池,以盐湖之利夯实边境,充实军需,这是升允在陕西总督任上给陕甘人民办成的又一件好事。郝玉秀所在的营防不久即开拔驻守在盐湖附近,此举既保证了新军的粮饷和边境的安宁,又让周边百姓乃至整个西北的各族百姓吃到了价格相对低廉的食盐。
郝玉元自然不知道郝玉秀已经在兵营里面谋上了差事,他心心念念地去盐湖贩盐的想法仍然没有就此消除。直到罗渠一个去盐湖办事的人把新军把守盐湖的消息带回来,郝玉元对于兵营的恐惧才让他彻底打消了这个念想。
郝玉元问来人:“关锁,现时兵勇把守盐池,咱这百姓民人还能去贩盐?”关锁道:“郝相你就不要想了,现时都是有门子的人才能进去贩盐,咱都是平头百姓。你一个熬活的人,更是去不成。”郝玉元决然想不到自家的弟兄就在盐湖的把手新军中当书手。郝玉秀此时也没有得到一点关系郝玉元的消息。弟兄三人自从分别之后,至此没有见过彼此。
郝生贵已经能帮着打草放羊了。这一日后晌,个子低矮的郝生贵打了一萝草背着,赶着羊群进了山梁,半道上遇到村里的白喜娃,喜娃挡住郝生贵,非说生贵的草是自家山梁的。生贵觉得好笑,用浓浓的陕北口音道:“这七梁八峁上的草都长得差不多,凭啥说是你家的草。”喜娃想不到这个小娃娃说出这样的话,这反而让他一个大人不会说了,只好支吾道:“这就是我家的草,反正……就是我家的!”生贵道:“你说是你家的?你叫一声先看草能答应你?”喜娃脸憋得通红,羞恼难当,就把生贵的草连同草篓一起抢了去,顺手抽了生贵一个巴掌。
生贵一边哭着一边把羊赶到东家的窑洞里。饶忠厚见生贵哭,就问娃出甚事了。生贵学说了一遍,气得忠厚直跺脚:“我寻他狗日的去!这老东西太不要脸了。”郝玉元却道:“东家,算了,一个娃娃家被打几下也没有甚事。不要弄得你难做人。”忠厚却道:“这事情你不用管,这是我跟白喜娃的事。欺负人欺负到我头上了!在这罗渠村还由了他了!”
忠厚领着生贵找到了白喜娃:“喜娃,你如今这本事大得说不成了。”白喜娃瞪着眼睛道:“咋哩?”忠厚道:“好而无干的,你打人家娃娃干啥?还把草篓都拿回你窑里了?”白喜娃道:“凭啥说是你的草篓?你叫一声它答应你哩?”忠厚笑道:“我把你个不识数!你不看篓底子写谁的名字?”白喜娃不说话了。忠厚知道,白喜娃是因为郝玉元不给他帮忙犁地嫉恨上了,故意生事哩。忠厚道:“生贵是郝相的娃娃,也是我的长在,他做错了事情由我打骂都在情在理,你凭啥打人家娃娃?再说了,你一个大人,又是本地庄户,欺负人家外来人的娃娃,还要脸不?”白喜娃再不说话,把草篓交给郝生贵:“给!”
郝生贵道:“还有我一笼草!”白喜娃道:“明儿我给你割一笼!”郝生贵道:“你头低下,我给你说句话!”白喜娃低下头,郝生贵一个脆生生的巴掌打上去,白喜娃一愣,继而大怒:“你!想死哩!”郝生贵也不恼:“你打我一下,我还回去,这才算两清了。”在一旁的饶忠厚也目瞪口呆:一个小小的娃娃,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这娃娃将来不得了!
饶忠厚回家把寻白喜娃的过程给郝玉元学说了一遍,郝玉元也颇感吃惊。到了夜间,郝玉元家的窑洞里传出来清脆的巴掌声,郝玉元道:“逃荒逃难的人,命都没有了,争强好胜能干甚?咱现时在人家的窑里安身立命哩,以后不准再使坏!”郝生贵含泪点头。
郝玉元在罗渠两年时间,已经具备顶门立户的身量了。饶忠厚对郝玉元道:“郝相,你如今可能独立门户了。”郝玉元笑道:“说好的三年,我干够再走!言而无信,咋在这新地方立足?”饶忠厚笑道:“我没有看错人。”郝玉元道:“就凭我家娃娃让白喜娃欺负之后你说的那句话,我都给你多干两年!就算顶门立户了,以后你有甚事,招呼一声,我敢不帮忙!”
饶忠厚笑道:“郝相,你在我这干五年,怕是要后悔哩。”郝玉元:“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干过后悔的事。我在府谷南梁的时候,那么大三进院子叫乱兵糟蹋了,我连眼睛都没有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从来不会后悔。再者说了,在你这里熬活,总比逃难强吧?我把一大家子人从灾荒处引到活路上,一个都没有折,我这辈子怕是再没有后悔的事情了。”
饶忠厚这阵子心里彻底踏实了。说实话,忠厚确实担心郝玉元在这个时候就自立门户,他绝对有这个实力和能力,当然也有这样的强烈的想法——不想当地主的农民不是好农民。饶忠厚用最简单的庄稼人的直觉判断,就摸清了郝玉元的心理。但是更让他佩服郝玉元的是,这个人一言九鼎,答应熬完三年仍然可以继续给他家扛活,这就不简单了。饶忠厚二年来非常了解郝玉元的为人,这人一旦说了话,就是把自己的牙咬成渣渣咽肚子里,也要把话搁住。说白了,是一个非常顾脸的人。因此,他当然彻底踏实了。
郝玉元对于自立门户并不急切,他在没有了解这个地区的耕作特点之前,绝对不会贸然出走去顶门立户。仅仅两年时间,他没有做到对这里的土地完全了解,他还需要更多的体会和观察。他信奉自己长期实践得来的经验:成家好比针挑土,败家如同决水堤。一旦不慎,有可能这几年的辛苦就白费了,在这里的生存就彻底断了念想了。到那时候再回来给饶家熬活,可能就跟现时不一样了。至少现时的自尊是平等的,尽管是扛长工熬活,郝玉元却从来没有表现出自卑的念想来,毕竟是靠自家的本事说话吃饭,熬长工也熬得硬气;如果成家立户不成,二回反过头来熬活,那就是讨吃要饭了,做人上有了亏缺,自然就低人一等了。
想到了这一层,郝玉元想:这五年绝对不能走,等这一步错不了。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