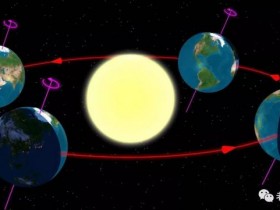郝玉元在饶忠厚家熬活,在罗渠算得上是极少有的事情了。因为罗渠并不是财东集中的地方,更不是富商巨贾云集的村庄,反而是罗渠很多庄户都在外面熬长工。罗渠一个长期在外熬活的白七宝的观点:“熬活就要寻大主家,咱罗渠地方小,尽都是些小财东,意思不大。”
白七宝曾经多次劝说郝玉元:“你跟我到大水坑走一趟,那里的财东羊群都有上千,土地整梁成片!你干二年长工绝对独立门户。忠厚这小财东吝啬抠门,嫑说你干完这三年,即便是再干三年都不一定能把门户立起来。”
郝玉元笑着问道:“白相,你干了几年了?”白七宝得意道:“不算多,熬了十六年活了!”郝玉元道:“那你现时在罗渠有多少地?羊群有多大?”七宝瞪着眼睛,有些不好意思道:“郝相我说你哩,你咋问我哩?我爱耍钱,这些年倒是挣了不少,大部分都耍钱输了。你是个仔细人,我是看你能成大财东的料才给你说这号话,旁人我还不稀罕跟他拌嘴磨牙哩。”
郝玉元道:“白相,咱吐出的口水砸出个坑,不能说话不算。我跟忠厚说定干三年,说成甚都得干到头。我从来没有弄过二茬子事。”白七宝听罢竖着大拇指道:“郝相你为人豪狠!我顶佩服你。”
时间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先后离世,年幼的宣统皇帝登基,清廷就日益显示出帝国末日的颓废和腐朽,各级官吏欺压良民愈演愈烈,加上乱兵、盗匪,民人们温饱尚不能保障,遑论顶门立户了。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农历二月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旱灾侵袭西北多省,其中以灵武、吴中、固原、西吉、海原最为严重。到了这一年的农历七月末,蝗虫遮天蔽日,将田间的青苗啃食殆尽。刚刚缓过上一段灾荒的民人们,又一次遭遇了生存的危机。
每逢初五、初十,在定边的红树林的粮市上,连荞麦皮的价格都涨到往年粮食的价位。
在外熬活打工的长工们早早就收了工,从外面纷纷回到罗渠。任凭财东们再财大气粗,再怎么仁义,在粮食紧缺且价官节节攀升的境况下,也不会让无活可干的长工们在家里吃闲饭。
郝玉元看到在外的“同行们”都回到了家里赋闲,自己也不好赖在饶家白吃白喝了。当然,以饶忠厚的家底供养郝玉元一家子三五年的吃喝嚼谷是不成问题的,而以饶忠厚的做人也决然不会把郝玉元一家子的饭菜停了。
郝玉元在某一天后晌把牲口棚里的粪肥堆积到窑洞门口,又从外面拉回来新土把里面垫平之后,这才回到了自家的窑洞里。他瓮声瓮气地对魏氏道:“今个你给我把饭做上,我从今日起不去东家屋里吃了。”魏氏没有多问,只应了一声。
郝玉元把自己的家底反复码算验看了几回:谷子、荞麦和豆子,各种主粮杂粮有个六千来斤,这就是近几年攒下的全部家当,另外还有三十多只羊和三十多只鸡,还有一群半大的鸡仔跟在母鸡后头到处追逐着落单或者小群的蝗虫。
千数斤的荞麦皮能撑住羊嚼多少日子?他心里全然没谱,蝗虫把地里能吃的草都吃完了,漫山遍野连一根绿草都寻不见,这羊彻底不能挡了。这二十只鸡的口粮倒是不用操心熬煎,满山遍野的蝗虫就够吃了。
郝玉元对于未来的生活思考了太多,他决计不会坐等着度过灾荒,而魏氏对于目前的困境并没有太多的愁苦。饶忠厚曾经来到屋里闲坐,见魏氏在喂鸡,随口问了一句:“老嫂子养了多少鸡?”魏氏道:“几个麻麻鸡,几个黑黑鸡,还有几个白白鸡。”忠厚闻言笑道:“到底多少只?丢了你咋办?”魏氏道:“丢不了。早起放了,晚上就回来了。”忠厚大约感觉到魏氏不太灵光,为了避免尴尬,便不再多问。
郝玉元一经决定不再去饶忠厚家,就言出必行,这是郝玉元做人的原则,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个原则。在油坊转给魏先生的时候,他说到做到,即使魏先生在灾荒过了之后坚持要还回郝家油坊的股份,郝玉元表示出了不容置疑的拒绝。
他时常问儿子郝生贵:“这世上甚最贵?”郝生贵道:“银钱最贵。”郝玉元笑道:“银钱不贵,只要有两只手,就不怕缺银钱。这世上说过的话是最贵的!”郝生贵不理解。郝玉元道:“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都收不回来了。再后悔、再不舍得都不顶啥了。说出来就要做到,做不到就不要说。记下了没有?”郝生贵点头称是。
这样的秉性固然让他在利益方面获得了极大地损失,但是无论是在府谷县城还是南梁塬上,郝玉元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他站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大写的“人”!无论多么艰难,他都不会违背诺言。所以,在感觉到目前的境况尚能过得去之后,他就彻底安然了:一家老小的生活能够招呼,粗茶淡饭能混个温饱,窑洞尽管简陋破烂,却也能遮风挡雨,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惬意和放心的呢?
整个沟梁上一片衰败的土黄色,偶尔有一点绿色,也被蝗虫密密麻麻地附着在上面。郝玉元用麻绳搓成的网子,每天都要抓回去大量的蝗虫,这让魏氏养的那几十只鸡生长得飞快。这群鸡每天下的十几个鸡蛋,完全足够自家日常的用度了。鸡蛋攒够一定数量,郝玉元就背着篓子去换钱换粮甚至换盐,竟然颇受欢迎。这群鸡反而成了蝗灾凶猛的时节上天最好的馈赠。
农闲生余事。村里耍钱的地方集中在白七宝的老窑里,这是一片荒凉中最热闹非凡的地方,人们把灾难带来的烦闷和抑郁全部发泄在赌场上,每天都有输了钱而过不起光景的主家,拄着枣木棍拖家带口外出要饭逃荒。
郝玉元从来不参与这些事情,在人们亢奋地喊着骰子的点数的时候,他在苍茫一片的黄土梁上钓黄鼠、抓蝗虫,或者背着装满鸡蛋的篓子、身上挂满了黄鼠皮,手上还挎着历尽艰辛挖来的甘草——这是在遭遇了蝗灾之后,沙土地里唯一幸存的出产了。郝玉元带着“盐池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中的两宝,在红树林的集市上拢着袖子和人讨价还价……
他积攒着一个又一个的铜子,又把这铜子换成一个个银洋。整个秋冬季节,郝玉元竟然攒下了十个银洋,而自家存下的粮食并未见少。连郝玉元自己都感到吃惊。整个罗渠村再一次轰动了——这个东边来的汉子给罗渠人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撼。
腊月初八的时节,郝玉元刚从红树林回到家中,正把第十一个银洋放到一个羊皮的褡裢里的时候,饶忠厚进了窑洞前面的院门了。
自从上次不告而别,饶忠厚再没有踏进过这个生机勃勃的院落。对于饶忠厚而言,郝玉元的离去,正好去掉了他心里的一块心病。当时的灾荒境况,省出一个人的口粮简直堪比正常年景里三个人的口粮!地里的庄稼都被蝗虫吃得连光杆杆都没有剩下,没有任何活路可以使唤长工。此时养活长工是一个稳赔不赚的买卖。
但是他决然不会提出让郝玉元离开的话,他甚至已经下定决心、打碎牙吞到肚子里充一次大头,让郝玉元在没有活路的灾荒年白吃白喝,但绝对不能落下“食言而肥”的话把。毕竟三年的合同是刚刚说定的,墨迹未干。长工完全可以遵照合同在家里熬满三年,无论灾年还是丰年——毕竟不是长工不干活,而是地里实在是无活可干。郝玉元的不辞而别正好让他纠结郁积的惆怅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两个人心照不宣,更避免了“话说到明处”的尴尬。
饶忠厚的不太厚道让他省下了粮食,却也丢失了主家的面子——一个财东反而不如一个长工心里会想事。所以,他觉得郝玉元当时离开,作为东家至少应该把话说明,甚至应该谦让挽留一番,这样才更能显示出自己的宽宏大量来。此时他实在觉得有些后悔,面子上更有些挂不住,在这寒风萧瑟的夜里,饶忠厚的脸上却是羞得通红。
他开门见山地把另一个事项说了出来,很巧妙地避开了彼此之间那个令人尴尬的话题:“郝相,你家的丫头今天该交上十四了吧?”郝玉元道:“丫头是光绪二十二年生的。过了这个年该十五了。”饶忠厚道:“前几日我婆姨的一个远房表姐来屋里窜亲戚,说起西湾的张家有一个后生叫作张广荣,今年十八岁,如今要娶妻进门,说到我这里,我思想来思想去,觉得你家丫头最合适。张广荣是你们东塬人,前二年从神木给舅家顶门了。你看?”
郝玉元道:“我一个外乡人,没有啥想法,你只说你咋打算?”郝玉元知道,饶忠厚绝不会为如此简单的一个说媒而郑重其事,其背后必然有更深一层意思。
饶忠厚这才笑着说出了这件事情的由头。张广荣原本不姓张,带着一皮褡裢的银洋从神木到了西湾的舅舅张刚家,给舅家顶门当了养子,改姓叫做张广荣。张刚家地土宽,算得上是西湾最大的主户,土地成片,牛羊成群。张广荣到了西湾顶门之后没过几年,张刚的婆姨就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这让张广荣的身份非常尴尬——张刚有了亲生的儿子,顶门的事情自然意思不大了。于是,张刚与张广荣协议,辟出一大块田地和好几座山梁的草场给张广荣,算是对他的补偿。
张广荣到了娶亲的年纪,却因为是东路人,与花马池本地住户生活上诸多不同,就愿意以土地换取一个东路过来的婆姨。
饶忠厚道:“郝相,你目下正好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在这里给人熬长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郝玉元的心头突然之间热起来了。经历了这几年的漂泊和辛苦,他感觉自己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若是这三年两头灾的日子再来上几回,顶门立户还遥遥无期,大丫头的年龄大了,婆家更不好找了。谁也不太愿意娶一个漂泊无着的人家的女子。
他当然不想让大女儿受委屈,因此决然不会再没有见到张广荣之前就答应这份婚事。于是,郝玉元提出要让张广荣到家里来一回再给回话。“总不能人都不见,就把我家姑娘嫁人吧!要是人不合适,我宁愿继续熬活受苦。”郝玉元的鼻孔呼出热乎乎的气息说出了这样的想法。
饶忠厚觉得这无可厚非,至少是要见了人之后再说成亲的事情。但是事情毕竟搁住了,郝玉元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给他难堪。于是,饶忠厚告辞回家,说定日子让张广荣亲自来拜访一回。
张广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后生,绝没有让人产生任何印象深刻的元素,这是郝玉元对他的第一印象,这样的面孔在陕北地界一抓一把。唯一让郝玉元感到心里踏实的是,张广荣见郝玉元正在用夯子打土坯,二话不说就挽起袖子帮忙。干活很卖力,且从其干活的熟练程度上看,这是一个极勤快的人。就凭这两点,郝玉元心里有数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说和,郝玉元与张广荣之间形成了默契,郝玉元这个自尊又自强的陕北财东、外乡的长工,和同样来自陕北那块土地的张广荣之间签订了协约。那协约是经过甘肃宁夏府花马池清军厅盖章确认的,“以后所纳钱粮,概由郝玉元按实际地亩征纳……”这块位于张贵堡曾家掌的原垦山地和低地一百余亩,成为郝玉元在花马池安身立命的资本,尽管这是以女儿的婚姻获取的。但是郝玉元坚持认为,这是自己一贯坚持“勤作善为”的为人处世原则的结果。
光绪三年(1911年)二月,郝玉元又一次举家搬迁,这次搬迁却与上次搬迁的心情大不相同,回首那段未知而迷茫的日子,此次搬迁让他的心里盛盛满满。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苦日子到头了!熬到头了!套着饶忠厚的牲口的犁耙把黄土翻上来的时候,在他把大量的汗水洒在被人家的地头、继而把收获的大部分粮食装到别人家的粮囤的时候,在他踯躅徘徊,在灾荒年不愿意屈尊在东家的窑洞吃饭而遭受白眼的时候……他就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苦日子甚时候是个头!今日,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花马池这个离家乡近千里的地方扎下根了!
郝玉元来到几十里之外的西湾。在这块土地上,郝玉元惊奇地发现,这里与陕北老庄子的地形异常相似!这让他产生一种错觉,总感觉回到了老家,唯一不同的是,原本的青砖大瓦房没有了。郝玉元并不担心,他一贯坚持的“双手不闲,不愁没钱”的原则让他有巨大的信心恢复郝家在府谷的辉煌。
他把在一处最大的平顶山峁上掏了几口窑洞,在丫头到了张广荣家之后,一家三口就在这个圆形的山峁上安家立业了。这个山峁有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圆峁。他站在峁顶环顾四周,蝗灾遗留下的一片光秃秃的山梁,一眼望不到边,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希望,再过两个月,这里将又是一片绿油油的草滩和旱田。不用几年,用自己的勤谨和坚忍的毅力,完全能再创造出一个富足的家庭。
尽管还没有任何绿草冒出地头,郝玉元仍然坚持每天赶着几十只羊在圆峁周边走一圈,那是一种类似于领地主权的宣誓行为,更是一种满足,一种炫耀,一种让自己内心充满希望的行动。
然而,他绝对想不到,郝氏家族将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比之前任何时代都要壮丽的辉煌事业。他更想不到,仅仅在新的土地上第一料庄稼收割完成之后,一直以来统治民人的清家就彻底歇火倒灶了。而郝玉元和广大的盐池的民人们,又要遭遇无尽的兵灾和匪祸。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