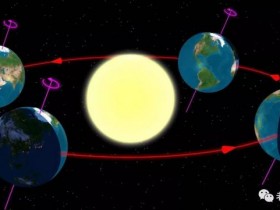南何村村委会门口一个人都没有,换届选举的通知已经贴了整整三天了,上面红底黑字写就的两个候选人的名字已经开始发皱,全然没有了当初的平展。我走过村委会一路朝西,在城门口的一户主家门前停驻,把户主二狗喊了出来。
二狗一边接过媳妇春娥递过来的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西装,一边穿着匆匆出门了。我俩相跟着要县城寻涛子说事。涛子官名叫杨明涛,跟我和二狗是一起耍大的哥们,当兵回来之后进了厂子,又从厂子下岗自己干建筑,现如今事情干得大得很。我俩寻他为的就是换届选举的事情。
这次换届选举的候选人里面仍然包括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何光明,另一个候选人则是何耀祖。尽管何氏家族是南何村的庄户,但是现时外来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何姓人当干部难免要在一些事务上偏向同族的人,对于外姓客户而言,这当然不能公平了。所以候选人名单出来之后,外姓人极不满意:这南何村仍然是何姓人的天下,咱外姓客户从来是二等公民。连耀祖这号不识数的货都能当上候选人,以后叫塬上乡党拿要尻子笑咱哩。
耀祖确实不识数,当年给他爷立碑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耀祖他爷何茂云死的时候享年七十一,耀祖他大何光定(陕西人不说腚,所以光定完全没有光腚的谐音的意思)十四岁,这原本是最好算的数学了——七十一减去十四,得出何光定出生那年何茂云的岁数57岁,然后用何光定出生的年份减去57,就能很简单地得出何茂云的生卒年份了,可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耀祖用了整整三天却得出了一个“他大十七娃十八”爷反而比爹年纪小的结论,这足足让村里人笑话了大半年。

何耀祖这两年跟着何光明跑前跑后,钱没有挣多少,却因忠心耿耿获得了何光明极大的信任。有一回何耀祖开车载着何光明出去办事,半路出了车祸,差点把两辈人手日塌到路上,何光明仍然对耀祖不离不弃。在何光明年岁渐长,精力不济的情况下,把耀祖扶上马送上一程是很自然的事情,却把村民们的利益送了自家的人情了。
村里人对耀祖当候选人非常不满,甚至包括很多何姓人,大家都说何光明“吃的官饭,放的司骆驼”。何光明显然早已经听到了这些风言风语,他甚至已经放出话来:“你们认为候选人不合适,可以自己提名嘛!”
提名不是那么简单的,选一个好的村干部,首先必须有能力,而且还要在道德上过硬。何姓人当然想选一个能干的何姓人上台,当然除了那两个人手;外姓人把村里人都码算遍了,算来算去,就算到了涛子头上,因为涛子算是南何村外姓人里面顶出息的人了。
涛子的父辈当年在县里上班,却早早过世了。涛子和他姐是老母亲一把辛酸一把泪辛苦养大的。涛子也算争气,一路上虽然各种不顺,却都凭着拼劲熬过来了,他不仅在县城买了房,还把母亲也接到县城里享福了。
之所以提名涛子,另一个原因是涛子从来不把何光明放在眼里,而且何光明也不敢在涛子面前把事情做得太过。涛子把老母亲接到县城之后,老家的庄基就彻底空下来了。这庄基跟何光明家连墙,何光明就想把庄基拿到自己手里,却又不想出钱,就打算以“废弃庄基”的名义将涛子的庄基收回村委。当时涛子正在赤水干工程,我连夜骑车给涛子报了信,他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工人回了村里。
涛子把庄基上的老房子推倒,然后就开始拉材料、打地基。何光明凑到涛子跟前有些尴尬地问道:“涛子回来了?”涛子说:“啊,回来了,咱不是还没绝户嘛!我大走得早,我还在这村里奓着哩。我听说有人要收我的庄子,就赶紧回来把房一盖,这两年门户不紧咯。”
何光明尴尬地咳嗽一声,给涛子递了一根烟,说了一句:“涛子兄弟,你这话就不对了,谁敢动你的庄子?只要我当一天干部,谁敢动你一把土!我叫他水漏完了都不知道锅打了!”何光明在涛子跟前下了个软蛋,让二狗看得真真切切的。所以在动议候选人的时候,就想起了涛子。
涛子把房子栽起来之后,隔三差五就回来一回,彻底断了何光明占地的念想。于是,何光明把目光转向了东边隔壁——队里的饲养室,三间的庄基很是敞亮。包产到户之后,饲养室连一疙瘩牛粪都寻不见,成了野猫和老鼠的战场。何光明耍手段把饲养室拆除,跟自己的庄基连成一片,成了南何村最大的庄基。
我跟二狗寻到涛子屋里,涛子很热情,不等我俩开口涛子就欣喜地问:“五娃最近干得咋样?啥时候盖房给我说一声,我派工队上塬!保险给你算最低工价。”我懊恼地低下头,道:“盖啥哩?我老屋的那间半庄子咋盖呀?”涛子疑惑道:“你不是说要换千五婶的庄子哩?何光明不给换?”二狗叹了一口气道:“何光明说没有政策,人家根叔和千五婶的两个儿子还在哩。”涛子道:“那倒对着哩。到时候你盖起来了,那俩货要是寻事就麻烦了,赚得说话哩。那要是朝东咋说?东边是豁豁的庄子吧?豁豁死了有十年了。”
我更不想说这烦心事,二狗就跟涛子解释:“五娃跟豁豁庄子中间不是有一道巷子嘛!何光明说里面还有一户人哩!巷子不能动。”涛子笑道:“说来说去就只准村官占庄基,不准村民盖房子!北巷子谁不知道?麦草走了新疆以后早都不回来了!这就是不想叫你盖房嘛!照我说,你就先不要着急盖,咱村里说不定要移民搬迁哩,你现时盖啥都是白盖哩!”
我和二狗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情,就赶紧打问,涛子说:“我也是听了一两嘴,说是咱村上能够得上移民搬迁的条件,政策可能还在研究。关键是何自力当年平整的那二百亩农田,镇上还不想放手,那可是旱涝保收的金盆盆!”
涛子说完又问我:“你现时啥打算?”我心烦地抓了抓头发道:“我有球办法,就想着换届把何光明换下去,选一个真正给村民办事的干部。所以寻你来,想叫你当候选人。”涛子笑道:“哎呀!我不想弄这事,我都多少年不在村里了。我干不了也不想干!”我跟二狗失望地看着他,竟然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按照我跟二狗以及其他外姓人的想法,这事情给涛子一说就成!
涛子给我俩续上茶水,道:“我不可能天天在村里待着,你俩寻我盖房,我绝对没有二话,寻我当干部,寻错门路了。”我跟二狗见没有回旋的余地就准备起身告辞,却被涛子一把挡住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咱弟兄三个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下馆子,喝一顿!”
我对涛子不参选感到很失望,当然也有些不忿,临走前我质问涛子:“你不选村干部,想一想对得起对不起白妮!”涛子愣怔了一下,欲言又止,随后转身晃晃悠悠地回去了。
我的想法彻底破灭了,可以想见的是:无论何光明继续当选,还是何耀祖当选,我的庄基的事情都不可能办妥了。唯一能够期许的是移民搬迁政策赶紧落实,到时候我的庄基和盖房问题就一并解决了。然而,即便移民搬迁,何光明或者何耀祖当选村干部,村民们的利益还是无法保障。
我给涛子撂下白妮的话,就是要他再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这事情就当我没说,如果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就知道怎么办。
白妮是何光明的弟弟何光亮的唯一的女儿,何光亮死得早,把媳妇和年幼的女儿白妮托付给了何光明照料,何光明当时信誓旦旦,胸腔子都拍肿了,他弟前脚死,他后脚就欺负起这孤儿寡母了。嫂子陈氏是一个软弱愚昧的人,尽管被坑了多次,有事依然找何光明商量。
白妮却很争气,也早都把何光明欺负她们孤儿寡母的本质看得一清二楚,她不止一次地劝说母亲:“我老大就不是个东西,你有啥事还爱寻他商量,被坑得还不够?”母亲却总是训斥她:“你碎鼻子娃娃懂得个啥?庹人的事情,你不要掺和!”
白妮跟何光明家的大妮年龄傍肩,两个人在一个年级念书,成绩却大相径庭,按说一个先人留下的基因,白妮冰雪聪明,人也漂亮大气,大妮却是个瓷锤楞种,皮肤黝黑,唯独身材臃肿,体重能顶白妮两个。
大妮处处不如白妮,虽然长得五大三粗,心眼却小得赛针鼻。她从小就不可避免地把白妮作为嫉妒的对象,而且白妮和涛子两个人好得如胶似漆,上学放学一起相跟着,这让对涛子极有好感的大妮更是醋意大发,她甚至散布谣言,说涛子和白妮如何如何,尽管涛子信誓旦旦地发誓,村里人仍然不肯相信,反而都说:“发誓不灵,放屁不疼。你发誓谁能信?”我跟二狗坚决地站在了白妮和涛子一边,尽管如此,白妮却仍然遭受村里人的白眼,也遭受到母亲的辱骂甚至毒打。
大妮利用其父的干部和首富的身份频频给白妮设置障碍,没想到白妮却愈战愈勇,一路逆袭,直到考上了县上的重点高中。涛子也考上了高中,为了避嫌,也因为家庭的原因选择了放弃,报名参军去了。
白妮参加完高考之后,在家里等消息,涛子此时已经分配到企业里当了工人,这于白妮的母亲也感到脸上有光,毕竟涛子是国家正式职工,彻底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两个人又一次遇到了一起,却更加情深意浓。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涛子正陪着白妮在南坡的沟沟梁梁里闲转,嫉妒到已经变态的大妮把白妮的录取通知书填到灶下烧成了灰。
白妮最终没能等到通知书,感到非常失落。而白妮的母亲却生病倒下了,她为了筹钱给母亲看病,只好负了与涛子的约定,远嫁到了四川,因此获得了一大笔的彩礼为母亲治病。然而,白妮的母亲最终还是离世了,白妮落了个人财两空。在临嫁的时刻,觉得仍然不够解气的大妮当着所有送亲的乡亲的面一脸得意地说:“你被师范学院录取的通知书,我填了灶火了。这下你到了四川就彻底安逸了。”
白妮面无表情,对这句话无动于衷。只有涛子气得额头上的青筋爆暴起,要不是众人拉着,满脸通红的涛子能把大妮剁成饺子馅。而原以为坑走白妮的大妮却没能如愿嫁给她一直迷恋的涛子,涛子妈说了:“我涛子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要你!你赶紧走,他回来非锤死你不可。”最终何光明给大妮招了一个外乡的上门女婿,跟大妮一样高的个子和身板。村里人都说:“这两口子能生出一窝洋芋蛋蛋!”
这么多年来,涛子永远无法忘记白妮,任谁都不能当面提起。即使我跟二狗这样的好友也不行。这一次,如不是遇到这种蛮缠事,我打死也不敢在涛子面前说起白妮。
选举当天,我看到候选人的表格上有杨明涛的名字,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