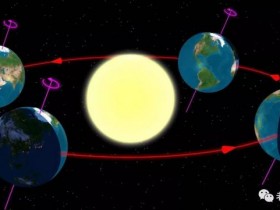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开春之后,整个盐池仍然没有下雨的迹象,其实,从上一年秋里开始,盐池县的民人们就陷入了一场干旱的恐慌中。干旱让盐池和周边地区的粮食颗粒无收,境内的山上一片荒芜萧瑟,牲口大量死亡。
粮食已经不是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人畜饮水成为当务之急。长久没有落雨的水窖里面已经干透,缺水的民人们牵着牲口排着长队在甜井子打水。每个人的脸上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色彩,嘴唇干裂。
在盐池地界,且不说打井的艰难,每每深达二三十米的井也无水可出,有幸打出水来,也苦涩咸燥,难以下咽,煮出的饭菜泛着让人心悸的黄色。而甜水井则是味道最能让人接受的水源了,尽管饮用起来依然咸涩。
无论白天夜间,有限的甜水井或者泉边都是人满为患,人们排队等着细小小的水流进入自己的器皿中。很多人因为一个两个人的位置而打得不可开交。
齐氏在最缺粮缺水的日月又一次进入了临产状态。这算是第三个孩子了。也许神婆的法力早已不足以庇佑,齐氏显得异常虚弱,瘦骨伶仃的身子几乎支撑不起高隆的肚皮。因为生了两胎,自认为能够完全自理的齐氏却万万没能想到:这个刚刚在自己的努力下出生的女儿会然她用尽了所有的气力。
看着刚刚下生的女儿,齐氏虚弱地对郝生贵道:“还没有奶水,你给我讨一碗水去。”郝生贵吩咐妹妹照看好嫂子,为难地捧了一只空碗出了窑洞了。在这个水比命还贵的时候,郝生贵不可避免地无功而返,当他捧着空碗回到窑洞口的时候,屋里传出的哭泣声让他如五雷轰顶。
齐氏完了!郝生贵一头栽倒窑洞门前,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的时候,生富告诉他,新生的侄女也完了!郝生贵一阵眩晕,眼泪就流下来了。
生活的艰难早已经让死人成为一种常态,不断有人因灾荒和灾荒引起的瘟疫而再也没能起来。远近的山峁上处处新坟,直到后来,人们连扎新坟的力气都没有了,满山满梁都是死掉而来不及埋进坟里的尸体,后来,牲口的尸体也加入进来,从远处看,白花花一片。郝生贵将妻女埋葬之后,甚至顾不上悲痛,就跟家人一起去寻找生计去了。
缺水的范围持续扩大,牲灵的大面积死亡更加剧了灾难的严峻程度。越来越多的灾民走南路下庆阳逃难去了,看着这样熟悉的场景,郝玉元慨叹不已,当年因为要活命逃难到花马池,谁料刚刚躲过一劫,刚刚浑全一点儿的家眼见的要被这灾荒弄得家破人亡,这天后晌,郝玉元对郝生贵说:“而今老天收人哩。这辈子我见过好几回了。这一回能不能挨过去,我看是艰难。而今要保住咱家的根,你得带着羊换儿逃难去。”
郝生贵当然不愿意离开这个承载了他童年的少年乃至青年的地方,更舍不得父亲和一家子亲人,他很不情愿的表情被郝玉元看得一清二楚,郝玉元语重心长道:“现如今人和牲灵连水都不保,你还犹豫甚!树挪死,人挪活,让你带着羊换儿走也是为了给咱郝家留下根脉,要不然都得干在这圆峁上!”
郝二娃年岁太小,带着逃荒无人照管,就留给了郝玉元和魏氏,郝生贵带着羊换儿和只需用一根扁担便能挑起的简单行李,跟随着南下的逃难队伍朝着一个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去了。
郝生贵带着羊换儿一路乞讨,一路打着零工,挨饿受冻自然是常有的事,大多数时候他们抢不过逃难的其他难民,当然无法获得更多的食物。郝生贵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羊换儿尽量避开逃难的主路朝着人烟稀少的地方行走。
这一日,郝生贵来到了甘肃环县一个叫作“樊家川”的地方稍微安顿下来,这个地方虽然山高路远,当地却民风淳朴,郝生贵便在这村中做“日子”打零工,晚上就歇在村后山峁的一孔没人居住的烂窑里遮风挡雨。
在樊家川暂时安顿下来之后,郝生贵逐渐与这里的人混熟了,因为干活舍得出力,又不弹嫌饭食,更不计较报酬,所以让他做工的人也比较多了。当然,遇到吝啬抠门的主家也是常有的事。樊家川有樊家四兄弟,住在砂石滩的老二樊海发最先关注到了郝生贵和羊换儿这对外来的父子。
樊海发也是苦日子出身,家里贫穷娶不上媳妇,长辈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了一个杭州的女子作婆姨,这婆姨面目丑陋却心地善良,贤惠能干,她把杭州人的精明和灵巧带到了樊家川樊海发的家中,让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土地面积逐渐扩大。
而樊海发脾气不好,因为婆姨相貌丑陋更不能生养,眼见着偌大的家业无以为继,樊海发只能用愤怒排遣内心的不甘和苦闷。最终生养无望的樊海发老两口,从慕家河慕家抱养了一个女儿。
郝生贵也逐渐了解了这村中的人情世故,所有的主家中,唯独脾气暴躁的樊海发为人最为豪爽,每回收下粮食,樊海发都要多给郝生贵父子一些,见郝生贵不好意思接受,樊海发就瞪着眼睛大声道:“郝相你家里日子艰难,多拿下粮食备用!这个年月没有粮食可不行咯。不要扭扭捏捏的不痛快!”
郝生贵成为樊海发的长工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农活样样在行,做事情又仔细又勤谨,最关键的是不多话,郝生贵对于樊家的大事小情从不参与,更不发表任何见解。他执拗地认为,给人扛长工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便是了,吃人家的饭,拿人家的粮,给人卖力干活,这是分内的事情,约外的事情不是分内的事情,所以不需要发表任何意见,更不需要参与。
几年下来,樊海发尽管脾气不好,任谁都骂过,却唯独对郝生贵极为尊重,别说咒骂,连一句硬话都没有说过。
伙计们有人跟郝生贵说笑:“郝相,你这人我确实服了,掌柜的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你。我在樊家干了十几年了,你是头一个。”郝生贵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显出不屑的神色,道:“咱就是干活的人,把自己的活干好就对了。”郝生贵说出的此一番话,让樊海发更加尊重郝生贵。
郝生贵从不闲着,从年头到年尾,农忙时候更是一个人顶好几个劳力,即使下雨下雪甚至农闲时候郝生贵都能寻见活来,活不离手。郝生贵在樊家一直“做活不要工钱,吃饭不掏饭钱”而毫无怨言。
羊换儿平日里做些诸如打草挡羊这样的工作,混一口热饭,年底还拿些口粮。父子俩总算在这里扎下根了。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5年),樊海发经过长期地观察和比较,认为郝氏父子实在与自家结亲最合适的人了。那一天天将将黑了,樊海发到了郝生贵的窑洞里。郝生贵正要起身迎接,却被樊海发按住了:“郝相我跟你说个事。说完你不要急着给我回话,啥时候想好了啥时候寻我。”郝生贵点点头。
樊海发道:“羊换儿跟秀英都不小了,俩娃娃是你从小看着一起长大的,我有意与你家结亲。招羊换儿上门给我做个女婿,至于传宗接代,多生几个娃娃,有我樊家的,也有你郝家的,你看咋样?”
郝生贵一听心里自然乐意:樊家治家严谨,家风淳朴,家道也算殷实,能跟樊家结亲当然求之不得。因而从来言语不多的郝生贵立即道:“东家我不用想,我现时就能答复你,这门亲事我乐意!”一句话让樊海发大喜:“那咱这几日商量一下具体的事宜。你有甚想法尽管说,咱把话说到明处。先说响,后不嚷!你没看咋样?”郝生贵道:“我听你的,我是顶没有主意的人咯!”
端午那天,樊海发宰杀了两只羊羔,约了郝生贵和族人、中人、邻人等一并到家中一聚,酒过三盅,媒人兼中人李守身起身道:“列位在上,今天是樊海发与郝生贵商议婚姻大事的日子,在诸位事主和列位族人乡邻见证下,敲定婚约,一式两份,永不后悔。”
根据合约,羊换儿更名为赫治樊,意思为樊家的半个儿子。之所以郝羊换儿更名为赫治樊,源于郝生贵不识字,只知道自家姓郝,陕北和盐池当地将“郝”发音做“赫”,因此合约上凡“郝”一律写作了“赫”,郝生贵就成了“赫生贵”,羊换儿也成了“赫治樊”,影响到后世孙子、重孙都因之姓了“赫”,甚至连郝生贵的墓碑上也讹写作“赫生贵”。直到郝生贵重孙回到圆峁老家寻根,这才解除了讹误,从郝小龙开始回归了“郝”姓。
合约签订之后,郝治樊一子顶两门,为樊海发老两口、郝生贵养老送宗,与樊秀英生下的长子长女都必须姓樊,若生一子具开两门,后世若多子就分两姓;若生两子,两姓不同家。樊海发将祖遗庄院、田产分为两半,水井、石碾子、石磨两家共用,立据为证。
郝治樊与樊秀英结婚之后勤勤恳恳,孝敬父母,养育儿女。郝治樊为人正派,少言寡语,勤劳善良,他与樊秀英生养了两子四女,按照入赘合约,长子给樊家顶门立户,取名“樊俊兴”,长女名“樊俊兰”,次子郝有君、次女郝莲儿、三女郝林叶、四女郝过叶。子嗣繁荣,也算是家业兴旺。
长女出生之后原本并不叫樊俊兰,因为是个女娃,郝治樊和樊秀英就忽略了忘了合约的约定,给长女取名“郝俊兰”,谁料郝俊兰长大成人之后一直多病多灾,多方求治而不得好转,后来有人指点,说郝俊兰犯了“口舌”,这才想起合约上的约定,改名为“樊俊兰”,之后身体竟然逐渐好转恢复。
郝生贵在儿子招赘之后就一个人在砂石滩背后的那孔烂窑里过活,在他看来,儿子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归宿,也算是老天长眼。他一个人受苦惯了,也耐得住清苦,平日里给东家熬完活,就默默地回到自己的窑洞里。
樊海发见状,心里极度不忍,这个性格火爆、脾气不好的西北汉子劝说郝生贵一起生到自家庄院里一起合家生活,郝生贵却道:“难不成我父子俩都让你养活呀!”樊海发罕见地对郝生贵发了火:“咋是我养活你们哩!你靠你的手脚挣下的!跟我走!”樊海发不容分说拉着郝生贵就到了樊家庄院了。
随着樊海发老两口的离世,郝生贵老人享受着儿孙绕膝的老年生活,他身材高大,相貌俊朗,留着半尺长的胡须,习惯性地用双手捋着胡须,他天生乐观,喜欢与人拉扯闲谈,生活再艰难也不放在心上,大概是经历了太多的人间惨剧罢。
樊家川初秋的早上,已经显露出丝丝寒意,郝生贵拄着拐杖穿戴整齐地出门了,他一路过梁越沟来到村中一个碾盘子跟前,那里早就聚集了一群人。庄稼收了,正处于农闲时节,人们闲来无事,聚在一起扯磨。
众人一见郝生贵来了,就都不说话了,只是看着他笑。一个说:“生贵叔给咱扯磨扯磨当年刮银川的事。”郝生贵清清嗓子,在磨盘上坐定,早已经有人给点上了旱烟,他捋一捋长长的胡须,抽两口旱烟,这才缓缓道:“清家的时候,整个陕北都打乱杆了,清家兵没有吃喝,见人就抢,民人们分两路往内蒙和宁夏逃难,一路上遇到豺狼都不算啥,主要是碰到兵匪和土匪。有一回,我们一家走到靖边一带,就遇上了土匪火拼……”
他把自己听来的内容经过加工,变成了吸引人们听下去的最生动的评书。因此,每当郝生贵坐在这石磨上开始谈天说地的时候,周边总不乏最忠实的听众。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郝生贵能说会道反而成了当地人最难以割舍也最感兴趣的娱乐活动。直到1973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人们再也没能见到这个身材高大的终年71岁的陕北老汉了。
而郝治樊却苦大愁深,艰难的日月和劳作让他过早地背负了沉重的压力,随着三位老人的相继离世,郝治樊和樊秀英两口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尽管老人们的离去并没有太多的痛苦,但是两人仍然觉得对三位老人有所缺憾。直到郝生贵去世的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才让他们跌入生活的另一种痛苦的深渊。
樊秀英绝对是养父脾气火爆、性格火辣的完整继承者,而性格相对绵软的郝治樊遇事不太出头,樊秀英于是成了支撑着这个家庭的灵魂人物。樊秀英是樊海发领养的养女,严格意义上说也并不属于樊家川人,郝治樊当然不属于这里,一个由地地道道的外来户组成的家庭,被村民们欺负是必然的。然而,郝治樊温和的性格,显然不能阻挡人们越来越过分的欺辱和排挤,而泼辣的樊秀英却每每能够让欺负他们的人目瞪口呆,并最终自取其辱。
二蛋作为砂石滩最难缠的人,是地地道道的村盖子,然而他一旦看见樊秀英,早就吓得不知所措,要么转身就逃,要么就绕道而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年近五旬的樊秀英偶然发现自家自留地的土豆被挖了不少,自留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生产队分发的粮食不够,全靠自留地来保证供给,如今自留地的出产被祸害,樊秀英火爆三丈。郝治樊苦心相劝:“肯定是二蛋干的,那是村盖子,你能惹过他?”樊秀英不依不饶:“他再咋说都是个人,他就是个蝎子,我也要拔下他的毒牙!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樊秀英在二蛋家窑洞附近拼命地谩骂,骂偷洋芋的不得好死,骂偷洋芋的是牲口养下的瞎瞎种……花样翻新地骂声听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二蛋刚开始还出来嘴硬:“老婆娘你骂谁?”樊秀英道:“谁应我就骂谁!”二蛋也怒了,上来要理论,却被樊秀英一顿连珠炮一样的叫骂气得脸和脖颈子憋得通红,路都走不稳了。骂人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成为了最具威力的武器,二蛋的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拿了二蛋偷的洋芋出来,樊秀英这下骂声更大,二蛋被自家婆姨起了赃,更无话可说,却无处发泄,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家婆姨打了一顿。第二日,二蛋被婆姨娘家的两个哥哥打得躺在炕上声唤了三天,从此再也不敢手长了。
樊秀英甚至对二蛋说:“以后只要我洋芋丢了,我就来骂你!”二蛋谁都不怕,唯独怕樊秀英,他每天都要在樊秀英家的自留地前待上好长时间,为得就是不让别人偷樊秀英家的东西,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郝秀英的性格在老年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个儿女的不幸让这个坚强的老人最终把一身的戾气磨平,而骨子里的倔强让她并未屈服于命运。
1974年,52岁的郝治樊和51岁的樊秀英的次女郝莲儿刚刚成家不久,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19岁,老两口欲哭无泪。9年之后,刚刚走出郝莲儿去世阴影的老两口又一次被命运捉弄,年仅33岁的郝有君与世长辞,留下妻子吴秀兰和一对儿女——郝小龙和郝丽霞艰难度日。第二年,郝治樊的长子樊俊兴也离世了,年仅45岁,好在孙子郝孝关、郝来明已经长大成人,而长子的离世更深地刺伤了两位老人的心。
在命运这样地折磨之下,郝治樊于1993年去世,享年71岁。1995年,小郝治樊1岁的樊秀英也与世长辞,享年72岁。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