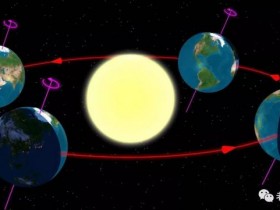郝陈氏对于大伯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哪怕一丁点的热心,她根本不关注大伯郝生贵所做的待在圆峁的决定,在她看来,大伯与其他来圆峁熬活的长工并无不同,如果说一定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长工并不合格。
郝娘对于丈夫郝生富的怀念是深入骨子里的,除了郝生富,其他人在她眼里都不值一提,再者,大伯郝生贵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尽管让郝陈氏对此没有恶意,却也绝无好感。
郝生贵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而郝陈氏勤劳能干,窑洞里外从来都是收拾得井井有条,几双儿女尽管从小没有了父亲,却也并不少吃穿,特别是穿衣,在那个年代,羊皮和粗布是做衣服的主要材料,一件衣服往往要穿很多年,一件羊皮穿大半辈子,甚至完了之后入土,还都要穿着。衣服的补丁自不用说,而郝陈氏几个孩子当然也不例外,无论是自己的衣服还是娃娃们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是无法避免的。但是郝陈氏的补丁也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针脚整齐细密,不似其他人的补丁,随便一块破布或者羊皮就贴上去了,看起来如同一堆破布胡乱编织成的衣服。郝娘认为,衣服是人的另一张脸面,就算是再破烂的衣服,也应该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郝生贵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私人物品在窑洞内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从外面扯磨回来,地上的一根绳头、半根铁钉都要捡回来放在窑洞里。他炕上的毛毡拥在一起,丝毫与平展整洁扯不上关系,上面尽是旱烟锅蹦出的火星烧起的小洞,铺盖更是随意地揉在一起,炕头的灰尘落了厚厚一层,也不曾抹扫。
之前郝陈氏还断不了隔几天去给大伯郝生贵居住的窑洞打扫整理一番,而不过两三天就又恢复原样,郝陈氏说过大伯好几次:“他大爹,以后要吃旱烟你就在地上吃,在炕上吃烟万一走了水(着火)可不得了。”郝生贵未置可否,只是看了郝陈氏一眼,该咋样还是咋样。
到了开春换季的时候,郝陈氏早就打发大儿子郝进财去红井子拉了几大桶水,她早就准备把几个儿女的布衣拆洗了。郝陈氏让郝生贵把衣服换洗一遍,郝生贵对于这个爱干净的弟媳妇显然已经相当不满:“金蝉蜕壳,有甚换洗的!”郝陈氏道:“换洗了收起来,来年穿起来也干净零整。”郝生贵却道:“这衣服穿不烂都洗烂了!”郝陈氏心中的火气已经腾起来了,却硬生生地压了回去。
郝陈氏对于与郝生贵与自己截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中已经毫无办法,说话轻不得重不得,最终只能不管不问,任他折腾。
经过几年的悉心经营以及羊群的繁衍生息,郝陈氏在圆峁牢牢建立了控制权,她已经有了一百余只羊,两头牛和一头驴。在当地人看来,这个女人绝不简单,在丈夫去世之后,郝娘能够依靠一己之力在圆峁扎根,甚至能够将一份家业守住并且做大,绝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恐怕一个男子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如此面面俱到。
郝生贵来到圆峁,其目的首先是要当家,作为郝玉元的长子,他几乎有着对家族天然的掌控权。郝陈氏的种种表现表明,这个家并非那么好当,郝陈氏并不会轻易把偌大的家业交给他。其次,郝陈氏在生活和生产上制定的一些规矩,让原本散漫的他极不自由;而对于他的合家的建议,郝陈氏从不答话。每每逼得急了,郝陈氏便带着两个儿子去弟弟郝生富的坟头哭一回,弄得郝生贵异常尴尬。
姬朝舟的清乡团又一次来到圆峁。十几个远近闻名的二流子,肩膀上扛着一把被称作“汉阳造”的步枪,领头的几个都穿着绸缎衣服,带着绸缎礼帽,斜挎着一把盒子枪。姬朝舟本人坐着软轿,被两个人抬着上了圆峁。
姬朝舟来之前应该早就抽了大烟,此时过足了烟瘾的他正眯着眼睛看着天,对于手下带他来到哪里,他几乎不得而知,此时的姬朝舟几乎是一个玩偶,被一群手下操纵着的玩偶,他的恶名成为这群人敛财的手段和依靠。姬朝舟手里拿着一只精巧的紫砂壶,这壶在整个边区怕也没有几个人见过,处于半昏迷状态。其中一个粮子对着圆峁的窑洞喊道:“谁是掌柜的?出来一个人说话!”郝生贵此刻早就不知道逛到什么地方扯闲磨去了,郝陈氏就从内里走出来,她见到这群人的架势之后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她不无讽刺地对着其中一个粮子道:“满仓你咋也在哩?闹红的时候,你不是在游击队吗?”其中一个叫作满仓的人羞红了脸不说话,众人看着他,他退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自从马鸿逵当了宁夏的省主席,盐池成了共产党的红军和国民党的白军争夺的地方,一直以来,双方谁也无法占领谁,双方力量在这里此消彼长。这种力量的不均衡造成了老百姓的苦难。共产党势力在这一带驻扎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稳定和安逸了;倘若马鸿逵的势力得势,老百姓就过得苦不堪言,各种税赋压得让人喘不过气,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就很能说明问题:生也税,死也税,拉屎撒尿卫生税。在上湾教书的任兰先生,尽管很久就不过问政治了,但是对于马鸿逵的队伍的苛捐杂税也是摇头叹息,反复揣摩的一副对联让他对马氏宁夏省政权失望透顶——从来不闻尿有税,如今只剩匹无捐。
郝陈氏当然对此并不陌生,如今马鸿逵的势力得势,多如牛毛的兵款和捐税必然要比之前多得多。果不其然,那来人就对郝陈氏道:“这二年闹红,你家的租子可是没有交够啊!”郝陈氏道:“老总,这事情可不怪百姓,我们没有交够我知道,这二年谁来收的?再者说了,我们就算把粮食驮到驴身上,交给谁去?”三两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
那人说不过郝陈氏,于是恶狠狠道:“郝寡妇,在这一片你是出了名的争,这在整个东塬都摇了铃了,任谁都听过你的大名。现时我不管你的理再正,你的话再端,我们该收多少,一分一厘不会少。你听明白了吧?”郝陈氏鄙夷地看着来人道:“那你这意思是刀架在脖子搜腰哩。你十几个大小伙子干啥活路不养家?非得干这欺负乡邻的营生,你们欺负我一个寡妇女人,也算是你先人给你积下德了,你全家就都能长命百岁,到不了阴司去?”这话已经是毫不客气了。在以往,郝娘都是用这种软硬兼施耍赖皮,甚至以“寡妇”的身份来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维护自己的劳作成果,大部分时候,这些人只能是空手而归,但是遇到外路来的清乡团团丁联合执法的时候,郝娘就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粮食被歹人拿走。

那一次,从南路来的清乡团与当地这帮子人一起来收粮,郝娘郝陈氏招数都使尽了,本地的团丁只是远远地看着她发表演说,外来的团丁不管郝陈氏如何说,根本不搭理,一味在窑洞里寻找值钱的东西,这一次,郝娘辛辛苦苦积攒的粮食和羊皮,全部被团丁拿走,郝娘哭天抹地而毫无办法。年幼的陈进宝不顾危险,追着去抢自家的粮食,抓着团丁的腿不让走,那团丁只抬一下脚,就将陈进宝踢到了郝娘身边的硬地上。陈进宝哇哇地哭起来……
郝娘见来的是本地吃粮的团丁,心里多少有些谱了,对付本地团丁,郝娘还是有一套办法的,正当郝娘准备用自己的独门绝技能拖就拖、能赖就赖、能少交不多交的办法的时候,郝生贵叼着烟袋从外面回来了,被这几个吃粮的挡了个正着:“你是谁?干甚来了?”郝生贵道:“我是这屋里的掌柜的!你几个干甚的?”原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把这次征收行动进行下去的粮子们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一群人开始围着郝生贵。
郝生贵当然也明白这群粮子来者不善,他看了看在软轿中迷迷瞪瞪的姬朝舟,抽了一口烟,坐在了门口的杏树底下。那个粮子跟着郝生贵,道:“掌柜的,一共是六十八块银洋,二十石头麦。”郝生贵瞪大了眼睛,道:“咋这么多?”那粮子软硬兼施,让郝生贵简直无法插言,平日里扯磨口齿伶俐的郝生贵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关键时刻竟然完全用不上了,郝生贵完全招架不住,最终答应按照定规缴纳钱粮。
郝陈氏对此极为不满,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在缴纳了钱粮之后,郝娘近二年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算是交代了。郝娘与郝生富在此事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任何人前来劝说都无法挽回。包括郝陈氏娘家兄弟老二来了,也不能让郝陈氏回心转意。郝陈氏决绝地认为,大伯郝生贵无法担负起当家人的责任,不仅不会让整个家族兴旺发达,甚至有可能让郝家在圆峁越发陷入穷困。
郝生贵对此也很生气,他认为,能把这帮吸人血的粮子打发了,后面的日子就安生了。郝娘却说:“用缴纳钱粮让这些人安生,无异于抱薪救火,薪不尽则火不灭。等到家里连隔夜钱粮都没有了,就算请他们来他们也不会来了。”
郝生贵感觉自己明显受到了轻视,他作为郝家的长子,当年被逼无奈逃荒怀县,如今家里兄弟不在了,自己从怀县赶回来,理应成为郝家的一家之主。现在弟媳妇不接受自己,实在是让他非常气愤,于是,他留下了儿子羊换,只身回到了怀县。而羊换也在半年之后,离开了圆峁。郝娘又一次独自承担起了家族复兴的重任。
然而,形势越来越复杂,任凭精明如郝娘的人也无法预料明天早上醒来之后,究竟是谁管理着五区这一大片地方。夜里,狼群就在不远不近处的山梁上嚎叫,有时候大白天也在羊群附近转悠,指望郝进财这个半大小子去放羊已经越发危险了。郝娘无奈之下,只好请二女婿张应贵来圆峁当差八年,双方约定,八年之后,任由张应贵带着儿女回平庄过日月。
然而,就在张应贵当差的这几年里,郝娘差点丢了性命。因为姬朝舟成为国民党花马池的乡公所乡约之后,又兼任国民党花马池乡公所的清乡团团长,郝娘因为屡次违反国民党县府缴纳钱粮的政令,又与红区的八路军联系紧密,姬朝舟就打算从郝娘着手,想一举捣毁我党在当地的地下组织。一场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即将在盐池圆峁和西梁展开。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