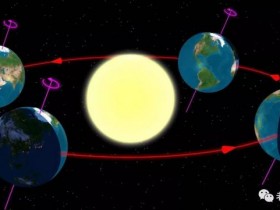夜深人静,天已经黑透。何官仓坐在自家二门口的门槛上发呆。他大何卫民就坐在他身后不远的小凳子上,他妈则给八仙桌的神龛上了四根香,嘴里念念叨叨地坐在了八仙桌旁边。
官仓脸上满是愁苦:“给我看病已经欠了一大笔钱,现时结亲还得一大笔,你俩从哪哒弄钱呀?”何卫民吧嗒地抽着旱烟,一脸不在乎:“父母欠儿女一桩婚事,儿女欠父母一副寿材。这是少不了的事情!”老娘道:“对着哩!你都三十六了!给你的事情没有办到头,我跟你大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
官仓却不以为然:“给你说了不顶用,没有任何意义,你俩这不是白花钱哩?我不能给你老两口养老送终,你俩也不必再为我操心了!谁不欠谁啥咯!”老两口面面相觑,良久,何卫民才说:“官仓我娃,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跟你妈还要在村里活人哩!咱能叫人看不起?”
官仓笑了笑说:“大,你一辈子精明,在两件事情上最糊涂,第一件就是给我看病,第二件就是给我娶媳妇,你这是把钱往水里撂哩!连个水花花都看不见,嫑说听见响声了!”何卫民听罢终于火了:“这屋里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我说咋弄就咋弄!不容你多嘴!”
官仓犹豫了一下:“大,不是谁说了算的事情。这是谁有道理的事情!”何卫民怒道:“在这屋里,老子就是道理!”官仓坐直了身子,欲言又止,他叹一口气,轻轻地下走了台阶。何卫民不放心,撵上去问:“你弄啥去呀?”官仓头也不回:“我寻五娃谝一时!”老娘在后面叮咛:“早些回来!都这时候了。”
五娃起来尿尿的时候,从里屋就看见院子里有个影子,他披了衣服出来,就隐隐约约看见了院子里有个影子,吓了一跳,等他定了定神一看,见是官仓,这才舒了一口气:“是你呀!我当是谁哩,把我吓一跳!”
官仓在里屋坐定,五娃摸出一根烟递过去,官仓摆了摆手,五娃点上烟,然后在身旁燃了四根香:“你走了有一年了吧?还是为媳妇的事?”官仓点了点头:“十月初八整一年。”五娃接着道:“我听麻子六婶说,给你在东山里头寻了个女子,才刚过二十。”官仓道:“彩礼要到了近十万元!这还不把我父母坑死了!”五娃惊问:“多长时间了?还在她屋里哩?”官仓说:“有一个多月了。这年头风声紧成这样,谁敢马上就办事?今儿办事明儿偷了你信不信?”
五娃点点头:“那对着哩。这女子咋要这么贵?金粉喂大的?”官仓说:“那女子屋里弟兄三个,一双半光棍,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彩礼还不要多些?我父母凑够了彩礼,剩下的日子怕就只剩下还债了。”五娃听了频频点头:“那现时咋办?”官仓说:“倒是有个办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子了?”说完就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五娃,五娃想了想,道:“只要能让老两口回心转意。我豁出去了!”
何卫民果然有本事,他在南何村是极为勤谨的人,如果不是儿子得病和娶媳妇,他家在村里绝对属于好光景。所以,他要去借钱,还真有人敢借给,别说还给带了利息。所以,官仓结婚的彩礼钱就快就凑够了,何卫民一扫长时间以来的颓气,说话走路都有了力气了。
这一天早上,他去了一趟北坡,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丢了魂似的。只见他踉踉跄跄地回了屋,喘着粗气说不完一句浑全话,把老伴急得转圈圈:“倒是咋哩!你说话嘛!”何卫民双眼发红,满脸泪水:“咱……咱娃……坟让人刨了!”老两口欲哭无泪,只能在院子里头干嚎。哭完嚎毕了,给官仓配阴婚的事情也算彻底拉倒了。
悲痛之余,老两口还是不停地托人找寻官仓被盗的尸体。过了一个礼拜,官仓的坟就恢复原样了。何卫民发现之后,实在是不放心,找了一个后晌,让本门宗族的几个后生,用黑幕布搭了遮天棚,把坟头挖开,开棺验尸,确认官仓静静躺在里面,这才放心。从那以后再不说给官仓娶媳妇的事情了。
这天后半夜,五娃起身尿尿的时候,感觉院子中有个影子,飘飘忽忽的,有些吓人,五娃壮着胆子打开房门,见官仓仍然站在院子中间。五娃把官仓让进屋里,在身旁点了四根香,这才道:“俩老人不给你张罗娶媳妇的事了,这下你彻底放心。”官仓道:“你跟二狗就是胆大!我就怕把俩人气出个好歹……”
五娃迷瞪着眼睛,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自顾自地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挖坟掘墓可是损阴德的事情。你狗日的可要保佑我俩哩。”官仓笑着道:“是我叫你俩刨我的坟哩,算不得挖坟掘墓。保佑你俩我还做不到,给你俩包邮几个鬼婆娘要不要?”五娃笑了笑,感到后背一阵发冷,他问官仓:“你在那边娶上媳妇了没有?”官仓道:“娶上了,那边好娶。咋?你真有想法?”五娃笑了笑:“实在娶不上,我也……”
听五娃这么说,官仓突然发怒了,一时间五娃屋里阴风大作,地面上的尘土飞起,把五娃吓得一泡尿生生地憋了回去,只听屋子里响起官仓熟悉的声音:“五娃,你好好活着!好好活人!人只要活着,啥事情都好说,再苦再难,也要咬牙活着!”
官仓的声音越来越远,影子越来越稀薄,最终消失不见了,屋里的风也住了,五娃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堂屋明堂的地上,身边那四炷香刚刚燃尽。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艺美网专栏作家。
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artmcn.com)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