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我先偷窃一段“百度”文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翻译理论,又称“三难原则”:信、达、雅。他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简而言之,翻译讲究“信,达,雅”;但不是每篇译文的作者都可以面对自己的作品如此自信。这些年来,我常常琢磨这句话的精义,有几方面的缘故。第一,我在考虑是不是需要阅读巴尔扎克全集中文版。巴先生的作品,我只是读过某些段落与梗概,心里一直很是向往或者耿耿于怀。第二,翻译出来的巴先生作品与其本人创作的作品是否一致。我们经常听到,“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以前有人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莫言表示,随便怎么翻译了。仔细想想,这翻译作品的质量还真是不好把关,除非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那如同拿着锥子用右手扎左手,字字珠玑,取舍之间,难于上青天。第三,一位作家用非母语写作,与用母语写作,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浏览过作家哈金(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写的《疯狂者》。我读起来感觉作者仍然是在用中式思维的方式来写作,换句话说,哈金的那篇小说好像是他在完成中文版写作后,将其直译过来的英文版。措辞与文字和张纯如女士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和“华人在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第四,我曾经梦想着翻译一些文章,但是只有想法,没有行动。由于对“信、达、雅”的敬畏,或者是我更沉缅于自己信手拈来的一些文字,相对自由自在——那是属于我的世界。况且,翻译别人的文字,除了要求对另外一种语言的精深认知,更需要对自己母语的娴熟掌握。思虑再三,这两者我都做不到,因此只好随手码几个字,敝帚自珍了。
然而对于日记,我并不陌生。我比较小的时候,课堂上老师要求写“日记”或者“周记”之类。日记上交之后,老师阅读并还略加一点评语。真正意义的个人日记大概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了。那时,我离开父母读书,偶尔记录一下生活的点点滴滴。虽不能像有些老先生(曾文公,蒋中正)每天雷打不动地撰写几句。但我一路走来,大大小小也有八本。这些形状各异的日记本子在当时来看都是比较“好”的硬皮或者塑料包装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设计有古代仕女图,“生日快乐”(大学宿舍几位老兄赠送的礼物),猫咪头像,国画(竹;是父亲一九七九年参加教育系统授奖大会的留念)等,不一而足。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本日记本扉页,我提笔写下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及“填写空白”的字样。另外一本是蓝色封面,竟然无任何标志,经过岁月洗礼,硬纸质壳明显磨损,显得历史沧桑感十足。离现在最近一本是黑色封皮,印有“日记·1999”的字样。这些日记本经历多年的风风雨雨,竟然没有遗失。那些年,我稀稀落落地记载着琐碎的事:大多是鼓励自己的话,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些小诗歌,几篇小说的雏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梦与如烟如缕的感觉。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到上个世纪末。我来到北美之后,猛然发觉作为“个人”的局限,在如此广袤无际的宇宙里,我是如此的渺小,便决定辍笔不再记录,下定决心从“无字处”记录。幸运的是,几年前,我得以机会把这几本日记本带来美国。现在,它们在书房的一角里堆放着—等年老昏花的时候,我再细细地品味吧。

提起日记,我不得不提一下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遯翁。方老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当然,钱老先生不会放弃他“幽默”或者“尖酸刻薄”的机会挖苦方老先生的。方老先生善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来褒贬”。“朋友来了,遯翁常把日记给他们看”。“知子莫若父”;知父亦有子。“鸿渐知道这些虽然对自己说,而主要是记载在日记和回忆录里,给天下后世看方遯翁怎样教子以义方的。” 钱老先生还分析了方老先生的心理活动:“因为遯翁近来闲着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这些记载从各个方面,各种事实来证明方遯翁的高人一等。他现在一言一动,同时就想日记里、言行录里如何记法。记载并不完全凿空,譬如水泡碰破了总剩下一小滴水。”
钱老先生甚至断言“方老先生”,并写道:“研究语言心理学的人一望而知是‘语文狂’。有领袖欲的人,不论是文武官商,全流露这种病态。”呜呼,写日记大概真的是种“病态”流露么?!例如,曾文公,蒋中正先生的确属于“领袖”级人物。那也应当属于“语文狂”了。只可惜两位老先生的“日记”命运迥异。曾老先生的日记(家书)广为流传。我自己买了一套,偶尔翻翻。蒋老先生的日记据说成了遗产,被争来夺去的。现在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存放,不见得轻易对外开放。钱老先生本人呢?据有人说,“钱钟书先生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数量非常可观,而且大部分都得以保存下来。……钱钟书少年时期在江南的日记,直至到清华大学求学时期的日记,在其晚年,都失而复得。……在无锡发现17册钱钟书遗失的日记。全是手写日记,毛边纸、大八开本,每本都可以看出是主人精心装订而成,封面左下部款署‘钱锺书’……钱钟书似乎很不愿意这批日记外传见世,没有答应请求捐赠的建议,连续去了两封信,并让在上海的侄子赶去领回了日记,物归原主。”不知道钱老先生当属他笔下的那一类人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钱老先生,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绝顶聪明,可以给自己解套的。其日记或许尚存人间,或许被其妻杨绛女士销毁,见得否天日,不得而知。
我记日记是一种爱好与习惯,是一种记录与倾诉。我没有想到示于众人;自己的孩子们汉语能力不够好,没有能力读,也没有兴趣去读的;C导对读我的日记似乎也兴趣匮乏。我的日记注定以后是要销毁的,如同我本人。日记本销毁大概会碎纸机罢,我不采用焚烧的方式罢,减少一点污染地球。本人的销毁方式,尚需上帝定夺。
我没有读过很多“钱”学的书。我猜测,钱老先生为什么称“方鸿渐”的父亲为“方遯翁”,可能是因为依据中庸之第十一章,“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从记日记的习惯和心态来看,“方遯翁”并不愿意“遁世”而不见知,而不悔。他虽是前清举人,但如同很多普普通通的人,他是要“入世”的。方遯翁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的今天,他的文字上的“本家”,据说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方方,在全球(当然包括中国)抗疫中声名鹊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主要缘于她的系列作品“方方抗疫日记”。
我知道“方方”其名,未曾读过她的著作。湖北还有一位著名作家,池莉。池作家的《来来往往》我听说过,是因为此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虽然我也没有看过。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过武汉,除了N年前做绿皮火车去邕时路过火车站,我下到站台一两分钟,感受一下“火炉”之魅力,再后来就是不时听到“汉正街”小商品批发市场。虽然我学过“武昌起义”的历史,知道“汉阳”造的枪,但我经常困惑于“武汉”与“武昌”,直到最近才理解了“武汉三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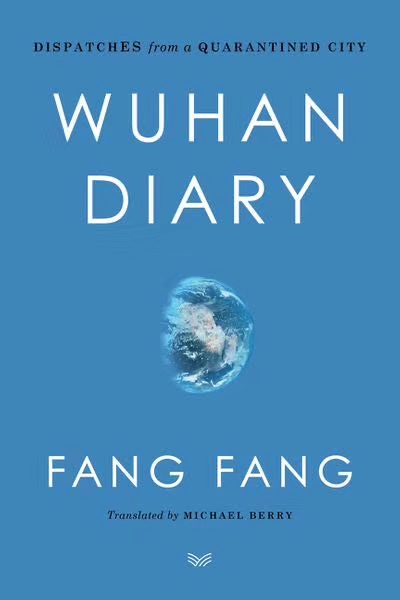
现在,作家方方准备将其系列日记在国外发表,英文的,德文的,等等。德文我不懂,英文书名好像是《Wuhan Diary:Dispatches from a Quarantined City》,销售日期为2020年8月18日。此日期是黄道吉日,大吉大利。我从小也有些迷信思想,潜意识里觉得这个日期是经过北京“白云观”里的道长或者“窦雪山”上的职业高僧指点过一下的—至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我对其书名迷惑不解。方方巨著的书名是“Wuhan Dairy”,即《武汉日记》。副标题中的“Dispatches” 一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派某人或某物去某地或为了某个目的。第二个意思是指有关国家或者军事的官方报告。“日记”与“官方报告”似乎有些出入,值得商榷。或者,我并不知道方方作家的本意。是新闻报道?是道听途说?是消息总汇?其中数字日期是否核实?这些问题希望方方能够在前言中予以解答,以正视听。
我本人从来没有读过方方女士的系列抗疫日记。我知道大灾大难面前,任何文字,图片,都会带来意想不到震撼的效果。2008年,我们一些热心华人在所在公司组织了一天募捐活动。那时,我看到了太多地震发生后的事情和悲剧。普通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至少是有感觉的。毋庸置疑,方方的“抗疫”作品“火”了整个华人圈。但也希望—或许方方已经明白,“日记体”与“报告文学”是不同的题材。前些年流行的“小屁孩儿日记体”小说系列大受欢迎,方方的“日记体”xx注定也会火爆,而且不需要任何广告——现在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每天的新闻发布会,世界各地冷冰冰的感染病毒者与死亡者数字如同“核爆炸”般威力地促销方方的作品。除了英、德文字之外,方方的作品可以翻译成全球所有的文字,因为新冠病毒会传播到地球上的角角落落。她好像也提到了很多人排队等候与她洽谈。这大概将会是地球上,除了《圣经》以外,被翻译最多的作品了。
“信、达、雅”,这是我的一点希望,希望该作品的翻译能够达到此境界,即使我仍然没有打算阅读她的这本书。荣誉与责任是等肩的。至少目前,方方的“武汉日记”不是其中之一,而是唯一。方方也不要束之高阁,以为翻译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高高挂起了。毕竟,这不是莫言的众多小说之一。
“不忘初心”,人生方能不枉此行。
作者简介:关东胜,艺美网专栏作家,工学博士(美国)、工商管理硕士(美国)。曾任教于京城高校,现定居美国,从事食品安全和品控工作。
关东胜先生授权艺美网(artmcn.com)发布本文,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