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拂风 280x200cm 纸本水墨 2023
拂风 280x200cm 纸本水墨 2023
画中宿镜——关于三年前见识朱建忠的创作
文/峯村敏明
译/高江波
对朱建忠的了解浅止于此:他出生于中国的江苏南通,在同省的南京艺术学院学习了中国画,此后便一直在南通创作。
最初和我介绍朱建忠的是東京画廊的田畑幸人。二十一世纪伊始,田畑便在北京798开设了一个新据点——“BTAP (Beijing Tokyo Art Projects北京东京艺术工程)”。一方面介绍当年有名亦或是无名的年轻艺术家,同时探索彼时中国艺术界的方向。据说某日,田畑注意到朱建忠玲珑两笔勾出的写意松树入木三分,便不辞千里来到南通探访。简而言之,拜访期间田畑对朱建忠认真诚恳的绘画态度印象深刻,同时也衷情于其为人。于是在2014年时,在BTAP为朱建忠筹划了大型个展。
就在前一年,2013年,田畑构想和发起的“新朦胧主义展”首展在也在北京 BTAP 开幕。朱建忠自然也应邀参加了展览,并展出了大大小小约 10 件作品。由于我也参与了这次展览的构思,所以我去了趟北京,借机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朱建忠的作品。
果然,细看详端下作品沁人心脾。它有一种与元代倪瓒一脉相承的静雅脱俗。不过,与倪瓒利用纸张皙白制造惯常的明朗不同,朱建忠的纸张则通体吸收了大量的墨色,如黑夜般深沉。可是观众之所以会被邀请进行这种跨世纪的比较,正是因为两者之作都品质极高。但同时,它们显得过于同时代脱离,感觉也算是种弱点。品鉴其画册,瞥见他在不久前还描绘了云雾、园石、假山和伫立于林中的僧侣形象。这印证了似乎有那么一段时期,他也尝试了青绿山水。但最终还是将一切舍弃,决定单用墨色来构成背景和松树(有时是冬日苍穹下的枯树)这些母题,从而达成了某种极致的冷峻。即便如此,可能还是有点不够,亦或许太多。我不是那种只喜欢新奇的批评家,即使这样,在当时九位参展艺术家同样毫不逊色的作品里,朱建忠的松树画鹤立鸡群,但难以言表其卓越之处。
然而,五年后的2018年3月,最后的第五回“新朦胧主义展”移步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的时候,我站在朱建忠高达四米的,漆黑的新作前目瞪口呆。这样的画必然是经历了某种决定性的事件。
 天外 34x45cm 纸本设色、丙烯 2021
天外 34x45cm 纸本设色、丙烯 2021
这次并没有出现某种让人称奇的新要素。相反,巨大的纸面被墨水全方位浸润,沉得深不见底。起初,我以为连松树或枯树的最微小形态都消失了。但是这绝无可能。从本质上讲,作为一个评论家我并不赏评毫无笔痕,单用墨色的禅意氛围(唯墨主义)。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也不会目瞪口呆。但我感觉到了。甚至在我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之前,脑海中的绘画史就在我耳旁低语,告知我罕见且微妙的事情——“这幅画里有一面镜子”。
当然,并不是真有一面镜子贴在画上。画面中也并没有任何镜的意象。而我之所以探知到 "镜子",从物理角度上讲,应该是察觉到处存在于似乎单色的整体画面中,只有账本大小的矩形小纸片,它们同样吸收了墨水,水裱帖服在黑白大屏幕上的各个角落。虽然它们一边与暗海的底色融为一体,另一边这些纸片,或许是因为亮度稍高,有些则是因为墨色太深,勉强躲过了背后大背景的遮挡,向我的眼睛宣告它们的存在。走近一看,原来朱建忠曾经画作中作为主角的松树和枯树,就在这些小小的纸片上,被悄然又确切地描绘下来了。
也许我这么写,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在形容“大画中的一扇小窗”。但是我们恰恰需要警惕,不要陷入轻率的比喻中。提起窗,作为西方绘画史中透视画法的开始,它指向的是视觉与深度空间之间的关系。从心理的角度讲,窗户也是一种唤起人们对“前面”或“外部”兴趣的装置。梵高画作中的描绘的浮世绘图案就是对窗外的远方向往的憧憬。正因为窗户的背后有着“视觉科学”和“浪漫主义”的辅佐,才造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电脑的Windows,免不了多少有点作为信息和计算的某种功利主义工具的冰冷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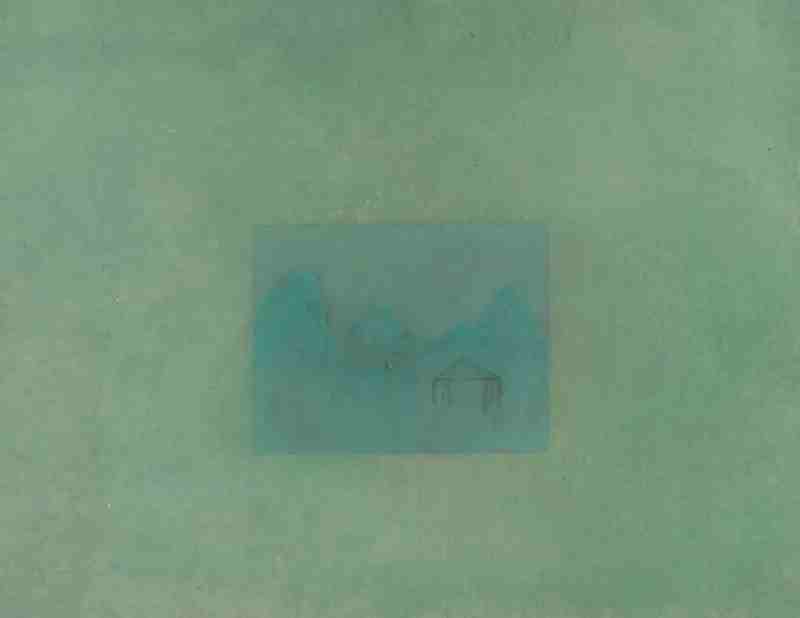 景明 35x44.5cm 纸本水墨 2021
景明 35x44.5cm 纸本水墨 2021
然而,朱建忠的画所表达的并不是“窗户”。散落在漆黑大画面上的小纸片,既不是告知我们“里面”或“后面”有什么的传递手段,也不是对异空间的浪漫主义承诺。然而,仅仅因为它们被放置在与观众视线平行的水平面空间上,即大画面平面的上下左右,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想象它们与亚洲,尤其是日本,在绘画被透视主导之前,附着在屏风和其他物体上的扇面画和长条诗笺(画和诗歌)具有类似的结构。这是因为在图画和诗文,出现在屏风中的情况(横向展开的生活空间)里,它们是一种鼓励自由地相互关联和共鸣,同时充满趣味的装饰元素。然而,在朱建忠的新作中,散落的小纸片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相互呼应。他笔下的松树和枯树,就像漂泊在大海上极其无助的小船,孤立无援,守着自己标记的位置,只默默发出肃穆的微光。
与雕塑不同,绘画原本是一种发展横向关系的艺术形式。但这些被朱建忠放置于墨海的小纸片却一反常态,它们拒绝展现彼此的关联性。至少,它们像是对这种阅读无动于衷。
那么,朱建忠那棵松树的孤影,连同承载那张扁舟般的小纸片,难道只不过是飘荡在虚空之海中的一粒尘埃吗?让我下意识感受到镜子的,并非这么简单的存在。乘于纸片船上的松树并没有生长在目之所及的横向现实空间里。它们也不急于以小纸片为窗沿,摩拳擦掌地试图通过窗户飞越到另一个空间。朱建忠的松树既不是横向扩张,也没有飞翔于空中,它仿佛在一口垂直贯穿自我意识领域之井一样的虚空最深处(而它的反面大概就是记忆)。它(树)落在一个镜面般的水面上,在那里,它毫无动摇地回送着我这般血肉之躯发出的目光。换句话说,那是一种将观者的目光引向意识深处的垂直力量,进一步讲,在意识之底有一种能把本就像是一体正反面的我和松树结合在一起,并瞬间送回的镜面构造。
 神居 47x66cm 纸本水墨 丙烯 2021
神居 47x66cm 纸本水墨 丙烯 2021
为何如此?通常,当我们望向现实中的镜子,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脸。但是,让我们确信“这是我”的,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意识之镜的介入。它在瞬间进行比较,并确认镜子中的“我”和意识中的我是一致的。没有这种意识之镜的动物,比如猫,就算将其带到镜子面前,它也会不爽地转过身去,不去看反射自己倒影的镜面。换句话说,意识底部镜子反射回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眼睛和内心都实际上看到了的东西——也就是,“意识”用我感知到的内容、我的心理经验去确认到的,对“记忆”的同一性确认。
不仅仅是猫。我们内心的眼睛(无需意识介入的眼睛)追随着三维空间中的事物和形态,将它们联系起来,从中汲取意义,并激起情感的波澜。即使是画家的眼睛,也主要是在这样的三维空间的坐标图上移动、测量,并根据情感对它进行改造。在这一点上,西方发展起来的透视空间、中国绘画的三远法空间以及日本和波斯等国的装饰性平面空间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即使是 17 世纪欧洲光学的发展,镜子作为复杂化绘画与观者之间的目光路径的小道具登场也好,或者在日本浮世绘中花魁舞得妖娆的手镜也好,镜子也都不过是现实视觉装置的延伸,要么在画面中横向传递视线,要么为画面和观者之间传送视线。因此,无论有无镜子,绘画主体也大都位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具有支配整个画面的力量。几年前朱建忠的松树作为每幅作品现实主角,也都当仁不让地位于近乎画面的中央。
然而,在朱建忠2018年 "新朦胧主义展 "的新作中,这样的绘画主体(松树)已经脱离了它曾经在画面上现实空间中占据常规的主要位置,被分配到了大画面中散落各个角落的小纸片中,像是配角般的一个小的空间区域。是不是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情况?从常识上讲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意识之镜”的状况,并将其中一项尝试带入思考,这就不是一种消极的状况,相反,我们可以将其评价为一种在绘画中少见的打破常识的情况。换句话说,在现实空间中降维了的松树,作为在现实中降维的反作用力,转移并下降到了观者意识空间的深渊中,成为一种与垂直凝视相对应的存在。它突破了绘画的主要原则——横向性(透视也符合这一原则),在镜子结构的支持下,插入了一条意识空间的纵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自抽象绘画出现以来发生的重大变革。
顺便提一下,那种抽象画是通过搁置(画面上不做处理)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形态和作为其反映的心理图像而存在的。与此相对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意识空间的纵轴,原本就是由反映现实形状的镜面为基础的,因此它既不排除画面,也不排除心象。主题仍可以是松树,或者枯树。这种绘画史上罕见的事件,我的确在2018年3月第五届新朦胧主义画展上朱建忠的作品中看到了。是不是要说我在夸大其词了?
虽然我认为这不是在夸大其词,但笔锋似乎有点激进了。那么暂时,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2018年第五回新朦胧主义展上,我看到朱建忠的作品时,为什么会直觉是一面镜子?这种被称为直觉的情境,既不神秘,也没有什么玄机,只是某种既往经验在意识中唤起了“相似”的声音。
就现在的“镜子”而言,如影一般贴近我记忆的是,最初同样让我感受到镜子结构已故日本西洋画家田渊安一(Tabuchi Yasuichi)的两个以大树为主题的系列作品《树》和《未完的季节》(1977-1981 年)。虽然田渊与朱建忠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我还是要从共同点说起。那就是“重复(反复)”。
 松迹五 34x46.5cm 纸本水墨 2022
松迹五 34x46.5cm 纸本水墨 2022
朱建忠的大画面中裱着的小纸片,是对构成画面的框架(框)的重复——不是空间里横向增殖反复,而是垂直向意识深处内化的重复。观者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暗而大的画面本身就像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而贴在其中的小纸片则与构成画作的虚构领域相似,并且让人自然地感知这种相同的结构的重复。这种相似性的重复为我们观者打开了一个激发了记忆的意识空间,让人回想起照镜子的经历。
与此相反,当田渊走出长达数年的低谷(在此之前,他一直致力于像窗户的比喻那种空间的多层化这类深刻的问题),对突然浮现的“大树”形象这一单一话题反复捕捉时,他的绘画超越了具象与抽象的区别,成为不禁同时打开了观者的眼睛和意识镜子的拥有者。
田渊原本擅长运用色彩的对比,而且在法国经历了“非定形艺术”之后,他认为绘画的精髓在于将脑海中的形象与笔触(不仅调动画家的头脑,还调动了全身整个身体的姿态)的结合。田渊在年过花甲之后,从自家窗外看到的大树并想将其作为绘画主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讲,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但结合朱建忠的松树,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不能说是巧合的共性。也许是因为对于每日相见的这一颗大树而言,横向展开和窗户的比喻都不适用,他觉得画中一定有某种可以洞穿内心深度的途径。没有人能预设这种情况,所以他后来的方法都是探索性的、试验性的。例如,在画面左侧边缘画一棵树,远处就重复画一棵与之对照的树。或者,将树和影阴阳一样并置。这是一种重复,磨灭现实感的重复。同时,也是某种取代现实感的神秘感的产生。而后,这些树影、大地和天空,大体都用颤动的笔触和补色关系实现。也就是说,作为事物的表象呈现,实际上不过是以空相为基础的色彩关系和不具有客观绝对性的画家重复笔触下的产物。同时作为绘画的真理,在一个宛如极乐般的光景中显现。
因此,乍看之下,朱健忠和田渊安一走入的是相反的绘画领域。然而,前者通过画框的重复(然后绘画空间本身的包含关系也形成反复)而后者将图像如“形影相伴”般的重复簇拥,在观者的意识中唤起了一面镜子,明确了绘画可以具有垂直的接受结构的节点上看,让绘画获得了适配纵深的受容结构。两者惊人的相似性超越了年龄、国籍、样式、材料等不同。
尽管如此,我的本意并不是只想说中日两国画家之间存在某些特殊的相似之处。这种极端的个例,连突变也算不上。
说实话,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宿镜之画”的情况,不可否定自古以来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作品中都潜藏着。相反,古往今来,任何能唤起某种神秘感的艺术作品,哪怕只是一幅赏心悦目的装饰画,也一定有镜子的元素。否则就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一幅画往往会激起非比寻常的感官刺激,在人心灵深处产生共鸣,使我们忘记了自己与他人(我们所看的对象同自己)之间的区别。可是,人们一直无法很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并试图用其他方法来衡量绘画的魅力。19 世纪末,这些具有强烈精神诉求的画家们所尝试的一种解决办法是,试图放下或搁置现实形式和心中的印象,换句话说就是走上抽象之路。然而,随后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这条道路以及于此相对的,固执的具象也都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势象 60x68.5cm 纸本水墨 2023
势象 60x68.5cm 纸本水墨 2023
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就是一个例子,他没有走这两条路,而是意识到绘画与镜子、图像与肖像的系统存在问题,并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到对其的阐明中。因为他年轻时曾因抽象画的局限性而转向,从而坚定地转向于具象和形象的探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玩世不恭的好奇心,以及不执著于确笔触的客观信仰,以及他身为西方画家那种对画面平面连续统一性的固执,都阻碍了他深入到图像的裂缝中去,从而最终无法意识到在他意识的底部存在着一面镜子,这不是图像的镜子,而是他意识底部的镜子。他无法进入由图像裂缝造成的情境深处,也就是无法最终意识到他意识底部的,并非图像性的镜子的存在,从而最终脱离了问题的核心。到底是哪部分不够呢?
总之,马格利特并没有意识到运笔本身的两面性。画笔既可以表现又可以擦除,但他只确认到画笔的表现能力(绘画的行动性)。就算他对图像与意义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形式否然相似性与图像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精心的考察,但最终他还是将所有这些都收敛到了一个表面上没有破绽的图像里。
话虽如此,也许是厌倦了这种隐藏笔触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马格利特突然引入了一种据说是雷诺阿风格的粘滞笔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画面那如磐石般坚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被破坏了。雷诺阿式的华丽视觉只是在加强,丝毫不见画面(垂直)断裂的迹象。没有断裂,也就导致画面也没有被反映在意识底部的镜子中。让他无缘于画笔的失误(被默许的失误)这种理性暂时熄火的体验了。比如 15 世纪禅僧世寿的《秋冬山水图》(冬景图)中奇异的竖线这种探索绘画奥妙的这些竖线,最终同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的重多完美无瑕的画作无缘了。
鉴于雷诺阿的特质,马格里特选择雷诺阿而非塞尚是有道理的。塞尚是西方画家中的一个例外,他以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实现了画面的非连续性,因此他晚期的风景画往往具有垂直组织观众视线,并将观众的视线引向意识的深处的力量。产生这种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是笔触的重复。
 墨影 70x68cm 纸本水墨 2023
墨影 70x68cm 纸本水墨 2023
在塞尚的晚期作品中,打动我们的不是他的笔画了什么,而是他仿佛在丈量自己与绘画对象之间这样那样距离时笔触的犹豫不决。就像在画笔上添加画笔一样,当艺术家进行这样动作的重复时,他不只是在观察对象,也不只是在观察画面上正在形成的图像的编织。显然,他的每一笔都是在与自身意识内部的镜面对话。由于塞尚的意识断层存在,他的绘画从来都不是一系列图像的统一,而是我们观者动员意识之镜后初步形成的有效回路,它让回复生效,从而形成主体与客体协作的画面。
埃米尔伯纳德,所谓塞尚“将自然视为圆柱体、圆锥体或球体”的说法,很可能是由于对塞尚如何形成割裂的画面缺乏了解的误读。然而,正如我们刚刚从马格里特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考虑到西方绘画中不可分割的以连续图像为主的固有传统,难免像伯纳德这样的天才误读这句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甚至对所谓立体主义的名家大腕们也造成了影响。无论绘画以何种三维形式出现,只要画家们只专注于将对象仅作为对象来描绘,绘画的深层真相就不会显现出来。
总之,无论是框的重复还是笔触的重复,无论内在的否定或反否定、抹去对象和重新召唤对象(维度转换)等这样的行为,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画家玩得转。尽管如此,从原理上讲这种方法对几乎所有的绘画形式和个体都适用。但阻碍这种可能性的往往是关于绘画的文化传统和教条。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证明什么,但有一个场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线条的颤抖,这经常可以在年逾古稀的老画家身上看到。当一个精神健康的老人努力在画布上捕捉一些东西,却又无法轻易做到时,他的笔触线条就会叠加。每当我遇到这些类似犹豫划痕的笔触时,我都会感动,都仿佛看到了超越了艺术史和艺术教条的真相。这的确是年迈导致的手抖,但它不是业余艺术。对于一位画尽世间的老画家来说,遗忘的时刻已经来临,此时建立在可见的事物上的艺术教条最后一滴也蒸发了,但他仍然出于一种自强意志,坚持对用笔的重复。
忽略老画家的例子也无妨。重要的是,古往今来的杰出的画家们似乎都超越了画面的横向构成,唤醒了纵向意识视觉,他们都在笔触的重复中达成了这一点,或者至少留下了一种预感,让绘画超越了图像的专制的,正是生产图像的那支画笔的工作。而缺乏对此理解,真是马格里特的不幸。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主人公朱建忠 2018 年的绘画,它不是通过笔触的重复,而是通过框的重复获得镜像结构这种稀有属性的。
框的重复这个方子本身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策略,从古老的画中画到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在美国绘画中的画面并置,我们可以辨认出类似的萌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其理念都是作品的意图和内容无法通过单幅画面完全表达,而多个画面的并置或包藏,能给观者的内部输出第三幅或第四幅混合画面,甚至某种否定性的空白领域。然而,由于所有这些都源于对图像过度的依赖下生成的方法,因此无法摆脱画面空间的物理视角。眼前的图像一旦被否定,纵向的意识之井的井底便只能生成供其他形象(比如影子)寄存的镜子。这比玛格里特比起来进步不到哪去。这就是为什么朱健忠敢于采用重复框这样的办法有那么罕见。画家为何敢于如此独辟蹊径?虽然可能不够确切,但可以尝试推理一下。
 神所居 52x76cm 纸本水墨 2023
神所居 52x76cm 纸本水墨 2023
据我所知,朱健忠在2013年首届“新朦胧主义展”和次年个展上的两幅作品,尽管都是中国传统的纸本水墨,但在画作品的主题——松树之前,纸张已经被浓墨涂抹,作品充满了摒弃世俗的阴暗幽静的气氛。尽管如此,这幅作品给人的整体印象却非常接近西方绘画(Tableau)中的场景。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作品是用坚固的长方形画框(可能是金属制造的)展出的缘故。纵观收录了朱健忠早期作品的画册,也有不少无法装裱的大型横幅作品,以及许多与框裱形式相去甚远的长卷和卷轴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营造了一个平静的叙事空间。可以推断,朱健忠在开始与BTAP空间接触时,迅速放弃了画面平面的横向发展,向主题与背后空间紧密结合的“Tableau”风格靠拢了。
毋庸讳言,“Tableau”的原意是指它取代了西方中世纪的壁画样式,是一种便于运输、可交易,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爱的“板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绘画中切断了横向发展的余地,带来了一种经得起正面凝视的结构。然而,这一历史时刻同时也与世俗市民阶级将宗教的枷锁从绘画中剥离的趋势相关联,因此从壁画到板画的转变并没有导致绘画的纵向发展,充其量只是符合皇室和富人虚荣的目光,其结果只是促进了厨房静物的主题化。当然,板画所确立的主体与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将支撑材料换成画布而不是木板,所带来的益处也并不会衰减。这在伦勃朗的自画像和苏巴朗的静物画(所谓的 "bodegones"即卡拉瓦乔主义)中也不鲜见。这补全了绘画作为高度精神性作品的形式性不足,并增强了壁画和卷轴画未能做到的独立性。事实上,看着朱建忠 2018 年前的充满茂密松树的纸本水墨,不禁让人想起伦勃朗那Tableau风格的自画像一般,让人对主体与背景之间的严谨联系印象深刻。
但我怀疑,正是这种与Tableau形式的接近,让朱建忠感到了危机感。从它的起源来看,Tableau不仅仅是绘画的“表面”,强调单个物体的性格。虽然它具有主体与背景一体化的优点,但其强化后的统一性往往会阻碍视觉和意识的渗透,强化其“神圣的不透明性”。这种特性更符合不透明的圣像(icon),而非绘画。如果强化这一趋势,朱建忠的绘画最终会对待像圣像一样,将松树作为绝对的、超越般的对象来仰视,这种情况是不该发生的,不,是不可接受的。
原本朱建忠把松树作为崇拜对象而彰显就是不可想象的。他以在自己的画作中彰显天、地、人和自然间的统一法则性为目标,从而将松树作为这种自然的代表招入画中。中国绘画比任何其他文明的绘画都更拥抱和践行这种试图让天地之气交融的态度和方法。因此,如果画家(朱建忠)痴迷于一棵松树,陷入跪拜的倾向,那将背景的暗度加深到非现实层次的程度,甚至到了三矾九染(让纸多次吸墨)的地步就毫无意义。画家的目的并不在于松树本身。一棵树孤零零地矗立在这苍茫宇宙之中,独立而充实到能与宇宙抗衡,这才是他想要表达的含义
 伫足 34x46cm 纸本水墨 2023
伫足 34x46cm 纸本水墨 2023
这个苍茫的宇宙在哪里?它不可能融入Tableau的框架。从根本上说,Tableau是一种将世俗主题与世俗背景紧密结合的形式。因此,框架(画内框)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坚固装置被赋予了重要作用。要让这样一个框架囊括一个大宇宙,或者说包容一个超越陆地意义上的想象空间,可以说是一种痴梦。另一方面,即使试着将松树缩小,反之,将墨海极度放大。在同一维度内对比的增大,两者之间的差异仍将保持在整数比率的范围内。将宇宙尘劫的比例带入绘画的二维空间,本身就是对《华严经》儿戏。
那么,怎样才能超越维度呢?将框不是横向而是纵向地重复,在框中建立一种包容关系。然后将主体与背景之间无限重复的包容关系投射到观者的意识中。
乾坤一掷,想出“框的重复”这一招,想必这也是朱建忠一开始就期望的吧。这是我于2018年3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看到朱建忠的作品,并在那里感知到镜面之后,时隔三年多的曲折,最终得到的结论。
2021年6月13日

艺术家简介
朱建忠1954年生于江苏南通
1982年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毕业
现为東京画廊+BTAP签约艺术家
现生活工作于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