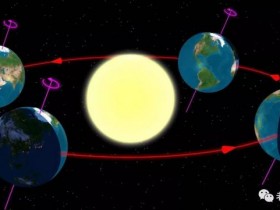可可今年五岁了,他当然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可可爸爸告诉他:“死了就是没有了。”他于是又把“死了”和“没有了”搞混了。街坊牛油逗可可:“可可,你的媳妇呢?”可可想说我还没有媳妇,但是总算新知道“死了”这样的词汇,当然想使用新词,于是他就告诉牛油:“我媳妇死了。”牛油哈哈大笑,逢人就说这孩子“人小鬼大”。街坊们就都骂他:“他家里那么惨,你也奚落他,还算人吗?”牛油就讪讪地笑笑,不说话了。
只有教可可下棋的司云钦爷爷知道,可可一定是把“死了”替代为“没有了”。他由此也联想到,这一定是可可的爸爸乐知杭告诉可可的,因为乐知杭晓得自己命不久矣。
可可一个人在家门口玩,那里有一堆盖房子剩下的砂石,里面混杂着树叶和狗屎,肮脏得很,没有街坊愿意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沙堆上游戏。而这正好成了可可的乐园。可可并不能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因为乐知杭病着,家里又穷,即使最瘦弱的孩子,也敢于欺负可可,可可绝不敢还手,因为没有人为他撑腰。当然,邻居们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跟可可玩,他们倒不是担心传染疾病,因为乐知航得的病并非传染病,邻居们担心的是传染了乐家的贫穷和厄运。
所以,可可一直都是一个人玩,很孤独,也一直都很沉默,但他也很快乐。至少这里是属于他的私人小天地,有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欺负和打扰他。
可可没有上学,他要陪着生病的父亲。五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时候,除去每天过来做饭,照顾爸爸,学下象棋,剩下的时间里,他就自己一个人玩。
眼见父亲越来越消瘦,喘气也越来越急促,可可却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乐知杭就告诉可可:“爸爸要死了!”可可瞪着天真的大眼睛,眨巴眨巴:“死了是什么意思?”乐知杭就说:“死了就是没有了。”可可歪着头想了想:“爸爸没有了?怎么会!我爸爸躺在床上。我有爸爸。”
他无法理解爸爸没有了的意思,他知道他有爸爸,有爸爸的话,爸爸就不会没有了,当然也不会死了。于是,他又开心地去沙堆上玩了。他实在太喜欢这个沙堆了。其实,对于别人的欺负,可可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有自己的快乐,有爸爸,这就够了。

妈妈呢?可可记不起来了。很小的时候,可可的妈妈就离开了这个家。爸爸就吐血了,后来就一直躺在了床上。尽管爸爸很虚弱,但还是很爱他,每次吃饭,都要给可可最好的。晚上也要给可可盖被子,可可很喜欢踢被子,从小就这样。
可可除了挖沙子,其他的时间就跟司云钦学下棋,他甚至很快就认识了象棋上的所有汉字。有一天,志愿者带来一箱方便面,可可指着箱子上的一个字告诉爸爸:“这是个‘象’字!”乐知杭惊奇地问他怎么知道的?可可说司爷爷的象棋上有这个字。
乐知杭最放不下可可。可可很可爱,也很聪明。这样的孩子成了孤儿,实在是让乐知杭心如刀绞。他在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火,打碎了床头供奉着的一尊佛像,嘴里大吼着:“拜你顶个球用!没见你保佑过穷人!”
可可从没看到过爸爸发火,可可不知道的是,几个月前,可可妈妈来过一趟,鼻青脸肿的,要带走可可。乐知杭当然不同意。可可妈妈自己也抱怨:“他给我的承诺都没实现,什么钻戒、手表还有大房子。他那么有钱……他都不跟我结婚……”当然,这些话她不可能跟乐知杭说,即使每天挨打,但是她也不会再回到这个贫困的小屋。
“那你活该,你自找的。管我球事!”乐知杭冷冷道。可可妈说:“娃跟着你不行!你一个病秧子,自己都顾不过来,把娃都耽搁了!”
“那我也不能让娃跟着一个从小不管他水性杨花的妈!”乐知杭有些歇斯底里了,毕竟他生病就是因为这个女人。“你把娃引走,就是把我的命要了。”
“你就半条命都不到了,要了能咋?”可可妈也不甘示弱。
“你还算是人吧?我的病还不是你恩赐的?你这女人蛇蝎心肠,娃更不能跟着你了。你为了自己,啥恶心事都敢干,无情无义,你把娃引走才是把娃耽搁了!滚出去!不要脏了我的地方!”乐知杭说完拼命地咳嗽起来,他咳出来的血已经把被子染得殷红。
可可妈还想说什么刺激的话,但是她也不敢贸然说出来,用语言杀人一般人看不到,现在却很容易实现,而这个女人却并不敢这么做。
“我还会来的。”她不甘情愿地离开了。乐知杭对着她的背影狠狠吐了一口带血的黏痰。
乐知杭毫无悬念地在进入腊月之后的一天早上离世了,可可当然不知道,他煮好了一碗白粥,从桌底的坛子里捞了一点咸菜,放到了乐知杭的床头木板上。可是乐知杭闭着眼睛,任凭可可呼喊,都没有反应。“爸爸,吃饭了!”可可最后一次努力大声地呼喊,连门外进来找可可的司云钦都听见了。
司云钦急忙跑进来,摸了一下乐知杭的鼻息,表情很冷,摇了摇头。可可却什么也不知道,他甚至给司云钦盛了一碗粥,招呼司云钦趁热喝。
司云钦看着双手冻得通红的可可,豆大的泪珠就掉落下来了。他握着可可的手,走出了屋门。
邻居们帮忙给乐知杭办了丧事,居委会也出面了。可可戴着孝,在沙堆上挖洞,然后把一个肮脏的小玩具人放进去,随后又埋起来,堆成一个土堆,甚至在上面插上了树枝。他看着大人们忙忙碌碌地进出自己低矮小屋,感到很开心,毕竟他的家里,好久都没有这么多人了。
乐知杭就躺在一个逼仄的客厅里,可可被众人牵来,按着跪下了,磕了头之后,殡仪馆的人就把乐知杭带走了。
乐知杭被抬出门的时候,可可就不干了,他拼命地去追:“把爸爸还给我!”他终于哭了。他追出去很远,却带回来了一顶乐知杭一直戴着的帽子。
乐知杭之前怕风,总是戴着一顶帽子,几乎从来没有摘过。刚才掉在了路上,可可捡了起来。
众人的眼泪都落下来了。可是,他们很快就又会恢复自己的正常生活,并不会因为认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的离开而感到有任何遗憾。
只有司云钦拉着乐乐的手,帽子里面有一张字条,司云钦把字条拿了出来,应该是刚刚写成不久的,因为字条比那肮脏的帽子显得很干净。这是乐知杭的遗嘱,他一直以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几万块钱,都做了交代,包括他后来完成的几幅呕心沥血的书画作品。当然,他把可可托付给了司云钦。字体是颤抖而且歪斜的,当然也可以看出乐知杭之前是一个书法很潇洒的人,
最后的手印必然是蘸着血摁上去的,对于病入膏肓的乐知杭而言,没有比自己的血更方便的印泥了。
之所以选择司云钦,是因为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人品又好,学识也高,之前和贫困又自尊的乐知杭是忘年交。所以,除了司云钦,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司云钦把东西做了统计,又请了律师和街坊作证,随后就带着可可远去了。去了哪里,也没人知道。
大概过了半年,有一天早上,牛油在菜市场看见了在街角缩成一团的可可,手里捧着乐知杭的那顶脏兮兮的帽子,沉沉地睡着。
“看来这孩子没少受罪啊。”牛油叹息着,他把可可叫醒,带回了社区。乐知杭的房子已经塌得不像样子,牛油就把可可暂时安顿在自己家里,可可看到了曾经的沙堆,高兴极了,他从沙堆里挖出了当年埋下去的小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童真。
牛油把乐知杭的房子修葺了一番,就让可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一天三顿饭自己支应。他甚至联系了一家学校,给可可报了名,费用当然是牛油出。街坊们知道可可回来了,也都过来看过几回,给过衣服和食物。
大家都说牛油大大咧咧的,没想到心眼这么细致。牛油也不听这些闲话,跟老婆商量:“只要家里能揭开锅,就一直帮衬着吧。别把孩子一辈子毁了。”牛油老婆道:“都听你的吧。”
司云钦一直没再出现,只是有一回在电视上,牛油看到了乐知杭的书画拍卖,一幅画卖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可可随时都拿着那顶帽子,晚上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抱着那顶帽子,沉沉地入睡,嘴角还露出了笑来。
作者:吉建军,字劳伍,诗人、作家、资深媒体人。
本文为吉建军先生授权艺美网发布,转发请注明来源:艺美网